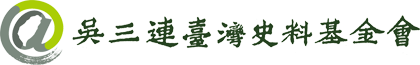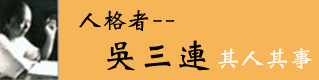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
梅心怡Lynn Miles 人權相關書信集 -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 張炎憲、沈亮 編 |
視人權為結果,而非過程
Human Rights as Ends not Means
1960年代晚期,國際鎂光燈開始聚焦於台灣政治犯的困境,但是跨國性質的人權運動卻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告成熟,並為當時的國民黨執政當局帶來持續性 的影響。兩股造成影響性的主流力量則分別來自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主要為日本、美國)與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以人權的高道德標準所進行的世界性良心犯救援運動。
1960年雷震和蘇東啟兩案發生後,只有來自海外學術界的零星抗議力量,消息並未受到國際主流媒體親睞,因此台灣獨立運動即成為爭取兩人獲釋的主力。 國際特赦組織自1961年成立以來即穩健的與時成長,驚人的成長速度加上與全球會員收取會費的運作方式,使組織總部擁有充足資金發展規模並進行完整調查工 作。國際特赦組織於1969年首次對台灣發起任務以蒐集政治犯訊息,此時組織已經有能力在亞洲任何地區發起持續性工作,不過要到1970年代初期,才開始 在日本、美國、德國等國家設立支部。
而1968年2月發生的陳玉璽案,則是首次不需透過海外獨立團體或是國際特赦組織也能達到救援目的之政治案件:在台灣執政當局指示下,前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UH)研究生陳玉璽遭到東京移民局不當拘留,並於隔天被強制送上飛往台北的班機,同年夏天陳玉璽遭判處7年徒刑,在川田泰代(東京)、John Reinecke、Aiko Reinecke(美國)等陳玉璽在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UH East-West Center)同學的奔走下,刑期很快減為3年,台灣警備總部也在陳玉璽遭判刑的6個月後,被迫召開一次對家屬公開,也對國際媒體以及一名東西中心代表公 開的審判。
儘管國際特赦組織在1970年代急速成長,但是秘密審判仍是政治案件的基本型態,而且一直不變的是,傳遞政治犯消息的活動者本身還是會被戴上紅帽子,或是 冠以叛亂罪名起訴,1971年李敖和謝聰敏遭到逮捕即是最好例證。經過將近10年,陳玉璽無端遭到起訴的案件,仍是國際壓力成功使軍事審判公開、最後獲得 減刑,而且家屬也迅速脫離特務監控的唯一例外。
直到1979年餘登發匪諜案的審理才能和1968年陳玉璽案的公開程度相提並論,但是這並不代表這流逝的十年間沒有任何進步,警備總部與其宣傳機關—新聞 局—反而是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觀察台灣內部的人權運動,可以從台北報紙報導的字裡行間中推敲出一些端倪,而當時的推測已在近年解密的戒嚴時期檔案中得到 確認,證實當時國民黨當局確實備受束縛,不得不根據世界認可的人權標準來解釋其所作所為。
1970年代上半葉,新聞局仍堅決否認台灣有政治犯的存在,但是局勢到了下半葉卻有突破性發展,1976年10月,國際特赦組織首度正式公佈台灣相關的調 查報告〈國際特赦組織簡報:台灣,Amnesty International Briefing: Taiwan〉,使得執政當局必須針對調查報告中對台灣違反人權的指控加以澄清。12月,行政院長蔣經國承認有254名他稱之為「叛亂犯」 (Seditious)的犯人,而將「叛亂犯」一詞解碼之後,也就等同於國際特赦組織所稱的「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
1977年國際特赦組織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則是另一項屬於該組織以及國際人權運動的成就,此番獲獎也使國際特赦組織在調查與言論自由、出版、集會相關事務, 以及提出公開審判與停止刑求等要求上享有一定的權力。另外,1977年卡特當選總統,美國外交政策朝向人權發展的劇變,再次重挫了擁護戒嚴者的銳氣。同年 Donald Fraser等美國國會議員召開的人權聽證會,使人權議題躍上世界版面,也使得國民黨執政當局如坐針氈,新聞局無法再將人權運動者詆毀為台獨運動的秘密傭 兵,更無法再製造台獨運動等同於中共滲透這樣的謠言,人權運動主義已經成為值得尊敬的稱謂。
人權運動者之間的國際網路也在1970年代急速成長,不分國籍的共同獻身收集台灣戒嚴體制下的秘密審判、政治犯所受刑求與非人道對待,以及監獄內部情況等 資料。其中像三宅清子即在內部暗中進行,James Seymour(司馬晉)、川田、Gerrit van der Wees(韋傑理)、Jack Hasegawa和Richard Kagan(柯義耕)等人則在公開場合活動,這也使得他們紛紛成為黑名單。關心台灣人權的正式組織同樣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如大阪的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 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東京的台灣政治犯救援會(i台湾の政治犯を救う会), 以及紐約的台灣人權協會(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和東亞人權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East Asian Human Rights)。在這些組織當中,特別是在對外界傳遞資料方面,台灣人士都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在本書中可以看到部分實例,但是也不能忽略王義郎、連根 籐、史明、王能祥、林孝信這些人的名字;更重要的是那些無視白色恐怖的壓迫,勇於公然挑戰使大多數台灣人陷於沈默的郵件檢查制度,日復一日的將秘密資訊送 出台灣的無名人士,他們的功績無法被一般大眾察覺,至今也仍未被歌頌。
從事人權工作的努力累積產生連鎖效應,成為一種自我供給的循環。1970年代後期,參與政治犯救援工作的成員穩定增加,工作中的風險也由所有參與者共同承 擔,使得人權救援在安全原則之下得以充分發揮,但是這並不是說可以完全不加以考慮風險性的問題,像是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隔年林義雄家中 的命案,1981年陳文成教授遇害,以及1984年劉宜良(江南)在美國遭暗殺都是實證,不過至少在1970年代後期,民眾已經開始參與挑戰戒嚴的集會活 動,公開示威已經成為政治圖像中的常態。
回顧過去的人權發展,從1970年代謝聰敏在孤寂牢籠中想要對外訴說案件事實仍充滿阻礙,到現在大眾出版品的自由流通,事實上是逐步經過無數次如史詩般的 行動才能換得這般成果,享受今日自由民主的我們,對於願意踏出這最初的一步,在同伴屈指可數時開始與國際組織聯繫的人權先鋒們,心中都應存有一份感謝,也 都留有一份虧欠。
最後我想說明的是,雖然我與台灣獨立運動者共同擁有「台灣人的未來應由台灣人自己決定」這樣的想法,但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將自由、公開(審判)、以及對民 主的高度關切視為最終結果,而不僅是達成宣示國家主權的過程,我看過太多空虛的「遠程」目標,也看到太多人批評中共惡劣的人權狀況,卻漠視美國將秘密竊聽 合法化,並且默許中情局對戰犯的刑求。我認為世界性的人權理當高於單一性的國家主權概念,如果我們能忠實於「人權至上」的理想,我相信不僅對台灣,甚至對 全世界的未來發展都能產生正面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