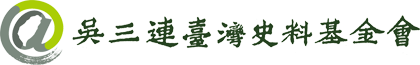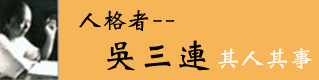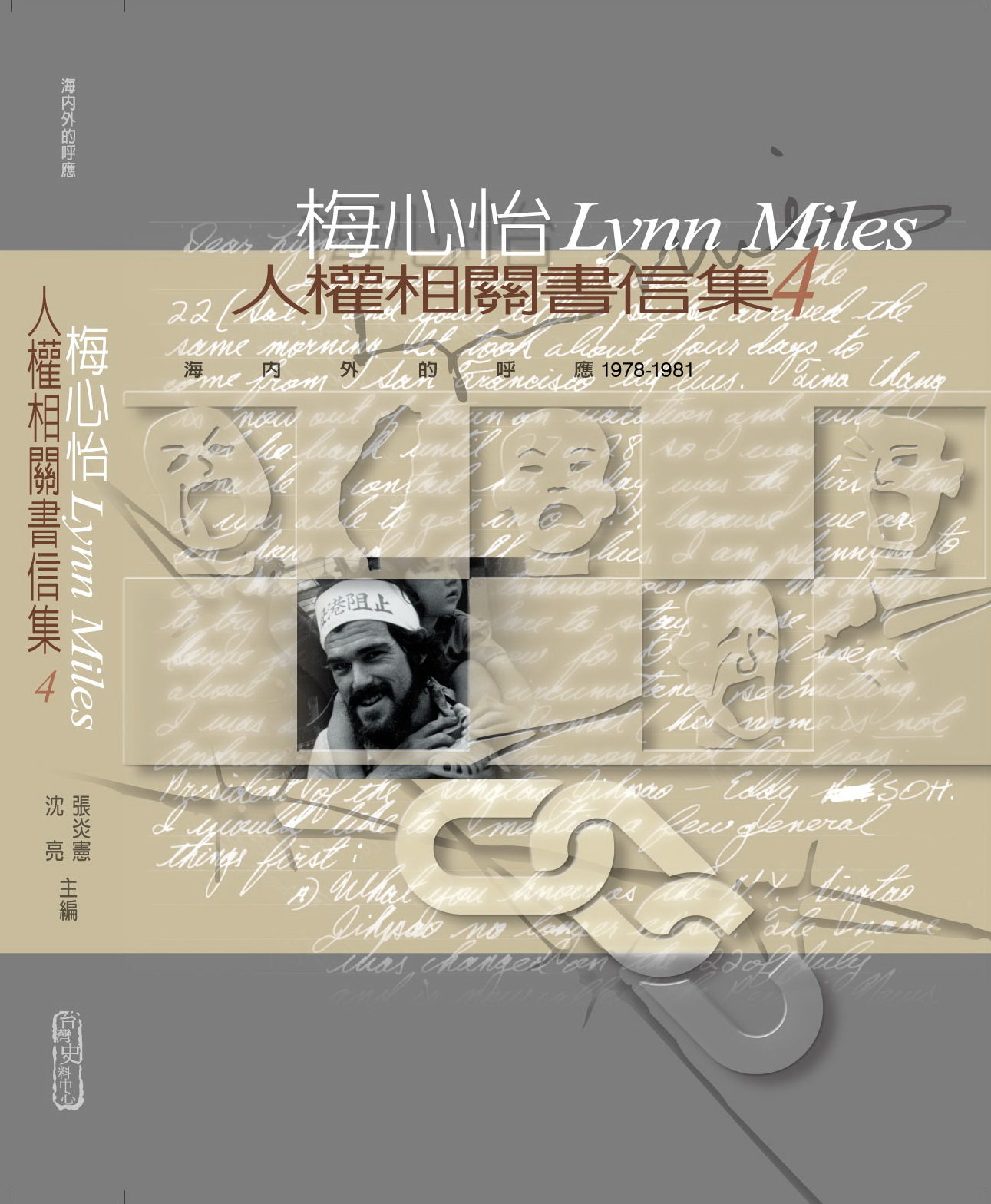 |
梅心怡Lynn Miles 人權相關書信集4 -—海內外的呼應(1978-1981) 戴寶村、張炎憲、沈亮 編 |
為什麼不能帶走男孩心中的那座鄉村?
文/梅心怡(寫於2011年)
在我成長的美國有一句俗諺,「你可以把男孩帶離鄉村,但是他永遠都還是鄉下人」,總是會有人把這句話當成一種堅定的信念,而我就是都市化「鄉村男孩」的活生生的證明,如果還需要更多的教條來支持這樣的說法,也就是「鄉村」,就是「城市外的任何地方」。
我在1950年左右,還不到青春期的時候就搬到紐約市郊區,我最先學到的是,這是個很難界定哪裡才是城市和鄉村交界的地方。但如果將「鄉村」(country)用國家(nation)-這個一大群人具有同樣認同,並宣示效忠-的意思來取代,那上面那句話還能用地理邊界來定義嗎?至少一定會有人認為,國家邊界的概念是固定且幾乎神聖,敵我意識分明,如果你在國界的這一邊,你就是我們的一份子,如果在另一邊就不是。有人會這麼說。
1950年也是一對夫妻,帶著他們的三個兒子,搭著家用的福特汽車出外兜風的日子。當他們打開收音機聽到新聞時,媽媽身體前傾,左右轉動著選台鈕,想要調到準確的頻率,很快的,車裡面就充滿韓戰前線戰況吃緊的嚴肅氣氛,原本坐在後座的大兒子,此時也將身體前傾,全神貫注聽著戰爭的新聞,並問說:「有戰爭發生嗎?」媽媽的回答有如晴天霹靂一般:「是的,戰爭本身似乎永遠都不會結束」。
接下來這60幾年來每天的發展,就像這回答一樣。但是,如果大兒子問的是:「媽媽,有對敵人的戰爭發生嗎?」母親又會怎麼回答?我猜測的答案是「沒有」。
同樣在1950年,在世界的另一端,一群孩子正被灌輸中華民國是人道典範的理想國度,什麼都有討論的空間,但是愛國不得懷疑。就像美國一樣,愛國主義是統治者哄騙民眾相信,只要在他們的名義下,沒有事情是罪惡的一種手段,在這裡,我們得到一個跨越太平洋的共識,那就是所有擁護國家的行為,即使是殺人,都是正義。
以下是這種手段的操作方式。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切都是輪迴,唯一的問題是哪裡是起頭。就讓我們從美國政府開始,他們的方法是通過法案和提供大量的資金給中華民國國庫,並給予一些該如何使用的指示。而一個眼神和點頭暗示代表的意義是:不用將所有的錢都花在得以讓蔣介石實現他反攻大陸承諾的軍購上(當時的說法是反攻,因為中華民國被殘忍且無恥的逐出中國)。(美國)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能執行這重大的責任,以及「為自由而奮鬥」的無私任務,並協助「自由中國」來武裝自己呢?順理成章的,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居於「民主軍火庫」這樣的領導地位,儘管像這樣的軍事援助,已經背離了「人道援助」,並受到獨特的待遇,但還是被許多人說成(支持自由中國)就是人道主義一般,而這是一種身為美國人的愛國心,為抵抗共產威脅,而要求我們要支援這場戰爭。
所謂「眼神和點頭暗示」,是指美國官方冷處理蔣政權(違法)對美國選舉活動的捐助,但是更重要的,蔣政權的目的,是在遊說國會持續對其進行金援。在太平洋兩岸的所有官僚都深深的意識到,「為自由而奮鬥」只是一種公開的消費,美援則像是一種賄賂、回扣、發紅包的行為,讓美國國會議員可以在鄉村俱樂部內遊樂,「租借」豪華遊艇,使全家享有最好宴會,以及免費度假住宿的會員證。諸如此類的累積,成為一種與為了自由奮鬥或促進人權無關的永久輪迴,每個牽涉其中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與權力。
就像影片快轉一樣,一晃眼50幾年過去,最近民眾占領華爾街的行動,呼籲我們要注意這些非常類似的作法。很久以前,有太多人假裝為了社會的共同利益而努力,但卻是以不法的手段來填飽自己的口袋。現在占領華爾街的群眾宣稱是為99%的人發聲,而支持力量傾瀉而出,表示99%這個估計雖不中亦不遠已,現在你可以看到這次行動,確實將美國人從舒服的沙發上喚醒,使他們移動屁股並伸出援手,這簡直就是奇蹟。
但是,對我們這些經歷以及學習到過去這50年台灣歷史的人而言,不僅是「被出賣的台灣」這樣的一個案例,也並不限定在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那黑暗的時代,這次是全世界都遭到了出賣(而且時間更長),情況到現在都還是如此。我們已允許這由無數小謊累積而成的巨大騙局,在我們的生活周遭繼續存在,我們受到紐約和其他帝國主義中心的歐威爾新語(Newspeak)機制的誤導,卻還在自鳴得意,而被導引進入一種矛盾的和諧之中,1週中有6天,我們習慣於相信,無以倫比的軍事力量也許是神所授予,殺人行為,只要具有崇高的道德理由,就可享有上天的恩允。「死了也比作共匪好」,必然會導向「唯一好的共產黨徒就是死的共產黨徒」這樣的結果,到了星期天,我們才告解,相信與其對立的事實:「沒有任何的謀殺是出自於良善的目的,而無論殺害一個人的罪惡是多麼的巨大,制裁的權利都屬於天堂」。2000年前,以眼還眼的法則,早被丟進歷史的垃圾桶,但現在的我們,是身處在什麼時代呢?
所以,誰該為此負責?為什麼會受到這樣的指指點點?我們都該負起這個責任,我們必須擺脫我們對於意見分歧,以及傳統封建國族的錯誤觀念,並以手足情誼的概念來加以取代,也就是,我們應容許有意見紛歧,但不可因為意見紛歧,而成為手足間戰爭的理由。但這並不是說如此就可以終結所有爭論,而只是終結那些不成體統的部分。我們可以盡情辯論,但不應使用武力,或指望任何人使用武力去解決爭論。
國族主義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我記得安排《雷震回憶錄》在海外出版時讓我陷入兩難的局面。當手稿經過陳菊的協助來到我手中時,我明白她是想要讓郭雨新來處理海外的出版,但是我同時也在1976年夏天,得到來自曾與司馬晉(James Seymour,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和杉原達會面過的人的訊息,這些人曾造訪台灣,並宣稱與雷震有過密切聯繫,表示在香港也許有其他比美國方面更符合雷震喜好的出版社。大約在那個時候,在大阪—台北這條路線上,有許多可以擔任傳遞物資或訊息的對象(有時我會跳上往香港的飛機,就為了和某位剛離開台灣,但不會來到日本的對象見面),可以和雷震作最後確認,或許會拖延出版的時程,但是大概不會超過2~3週的時間。
在每件事情都是透過第三、甚至第四手的轉達之下,我無法100%確定,雷震本人是否會有意見,但是一般來說,我認為他不會傾向於交給台獨陣營處理他的回憶錄。因為支持台灣人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就像他在《自由中國》中的主張)是一回事,主張台灣人有透過民主方式來決定自己未來命運,以及台灣和中國是,或應該是不同國家,則又另當別論。
我到現在仍有些懷疑。即使雷震存在著中華台灣民主國這樣的概念,李敖在1971年還告訴我說,可以將他的說法,當作是雷震的意思。李敖是支持台灣人有選擇自己未來權利的,而李敖認為,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給予自由選擇的機會,他們也許會選擇獨立,但李敖本人也並不支持獨立。但是,就像我說的,有很多不確定性環繞在我身旁,特別是雷震在撰寫回憶錄時的想法—這可能就是隱藏在這未出版手稿中的最好答案,但是我沒有花時間在閱讀回憶錄,而是在深入了解雷震過去所執筆的《自由中國》中蘊藏的意涵。雷震出獄後,雖然曾在家中招待陳菊、施明德與其他黨外人士,但是我認為這並不能算是為台獨運動背書,這項舉動的意義,應該在他入獄前,與李萬居、吳三連、高玉樹等人促進成立第三政黨類似,而雷震主張中華台灣民主國概念中的「中華」這個字眼,是在支持台獨的人士間所聽不到的。
統、獨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整個1970年代,海外人權運動人士為數不多,而他們設法在促進台灣獨立,以及推動統一之間保持中立、超然。統獨雙方或多或少都同意(每一個陣營都會有矛盾與衝突)支持—決定台灣未來,是台灣人所獨有的權利—這樣的概念。某種程度上,他們似乎將公眾對他們的信任,放在台灣內部真正表達自我意願的結果上,而我對統獨雙方都保持一樣的態度,但是有好幾次,雙方面都有讓我感覺到,忠於民主程序,看起來只是一種策略性的演練,對一些人而言,民主和公開程序的重要性,遠低於確定對他們有利的國家目標。外籍人士比較不會受到海外台灣人內部的社會壓力影響,司馬晉就可以作為代表,像我們就不會對台灣的未來應該如何決定這個議題發言,只是想促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場合,促成一個至少能在不需擔心遭到逮捕、刑求和長時間監禁,而能聽到所有聲音的環境。對人權運動人士而言,即使不時會倚靠某方的力量,但人民的主權仍是神聖不可侵犯。
我不能說我有堅持上述的立場而從未動搖—我經常引用「小而美」這樣的論點去支持台灣有主張自己地位的權利。但是隨著時間過去,我對堅持這樣的中立立場越來越有信心,而這也是1970年代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的唯一立場,幾乎每個參與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活動的人都能認同,大多數都還能進一步闡釋這樣的中立立場。我認為我們的成功,就是得到許多立場南轅北轍的對象的幫助,他們願意在基本原則下合作,呼籲在統獨爭議中要有所節制,所關心的,只是民主開放,和言論自由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