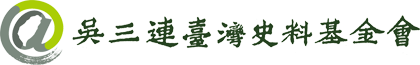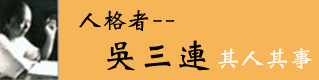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
《榮耀與寂寥》-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 導演:李泳泉 腳本:李筱峰 |
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
「鴻章下關去寫字,尾省台灣割乎伊,
咱乎清朝賣去死,害咱受苦五十年。」(福佬語)
1894年,滿清帝國為了朝鮮的主權問題,和日本帝國發生了甲午戰爭。結果慘敗,隔年,1895年,在馬關議和,拿台灣做為議和的籌碼,永久割讓台灣給日本。做為中華帝國的邊疆尾省的台灣,必須背負中華帝國的腐敗與落後的包袱,這似乎是歷史的必然。
然而台灣的仕紳臣民,對於這個歷史的宿命,並不甘心接受,於是成立了「台灣民主國」,與日本對抗,可惜功敗垂成。1895年台灣民主國失敗之後,前仆後繼的武裝游擊抗日行動,仍然此起彼落,讓日本當局應接不暇。大抵武裝抗日行動,多集中在日本領台的前二十年,從早期的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到後來的余清方、江定、羅俊等人的西來庵事件,都讓日本當局大費周章。然而,這些游擊抗日行動,多屬於「竹篙逗菜刀」的反抗,雖然激昂慷慨,但畢竟暴虎馮河,無濟於事。而且多屬於傳統的民變,不太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更難有成。
隨著日本領台後所實施的近代基礎建設,包括醫療衛生的改善;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貨幣、度量衡的統一;以及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公路等交通事業的積極建設與擴充;以及普及全島的基礎教育,使得台灣社會開始起了變化,武裝抗日運動也逐漸式微。除了1930年山地的霧社抗日行動之外,從1910年代中期以後,就不再有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代之而起的,則是1920年代蓬勃發展的具有近代性格的政治社會運動。
台灣文化協會可以說是1920年代台灣各項政治社會運動的大本營。要瞭解台灣文化協會的誕生,我們不能不從一群台灣留學生在東京掀起的民族運動的序幕談起。
民族社會運動的序幕
日本在台灣實施相當普及的初等教育﹐其目的之一在培養「忠良」的「帝國臣民」﹐然而這些為數可觀深受日本教育和文化洗禮的知識青年﹐有許多人反而成為1920年代台灣的民族運動的推動者與參與者。
在台北帝國大學尚未創立之前(1928年創立)﹐青年學子在受完中等教育或專科教育而想進一步深造的話﹐只能到島外去留學。當時留學生聚集最多的地方是日本東京。台灣的近代民族運動﹑社會運動﹐可以說是由在東京留學的台灣知識青年首度推動展開。而這些運動的展開﹐有其時代背景:
日本明治天皇末期及大正天皇初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到世界性思潮的影響,日本本土內部興起自由民權的思潮與社會主義運動﹐這些思潮與運動﹐衝擊著當時在日本留學的台灣留學生﹐為1920年代即將展開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埋下歷史的伏筆。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歷史的伏筆﹐在1917﹑18年頃﹐受到世界局勢的激盪而終於浮現出來。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推翻長達三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繼而同年列寧的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連1918年避居上海的孫文也電賀列寧革命成功。俄國革命成功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思潮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得社會主義成為1920年代世界思潮的主流。而且對於掙扎在被壓迫﹑被搾取的殖民地人民而言﹐俄國革命成功對他們無異是一大鼓舞。繼之﹐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T.W.Wilson發表了戰後國際政治原則的「十四點宣言」﹐其中所提到的「民族自決」原則﹐也帶給世界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極大的鼓舞﹐因此﹐大戰後,在歐﹑亞﹑非的一些弱小民族﹐風起雲湧地興起民族自決或民族獨立運動。例如﹐同樣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於1919年 3月發生了「萬歲事件」的獨立運動。3﹑4月間﹐在全朝鮮的618個場所﹐發生了332回暴動﹐以及 757次的示威運動;而隔月﹐中國也發生五四運動﹐掀起反日的熱潮;同年﹐愛爾蘭也獨立….。這樣的世界風潮,當然也刺激著台灣的留學生與知識份子。
1915年(大正4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總數約300多人﹐到了1922年已達2400多人﹐這些留學生在外接觸的資訊和思潮﹐思想大受啟發。
談到台灣的留日學生,讓我們想起這位當時扮演著「台灣留學生的大家長」,也是促成台灣留學生串連起來的一位關鍵人物-蔡惠如。
蔡惠如是台中清水望族出身的漢學家。他因為經營漁業,經常來往於台灣、福州及東京之間。相貌堂皇、身材魁梧的他,熱情奔放,浪漫重義氣。當身無長物,有著理想熱誠的留學生,正需要具備足夠資歷、財力、聲望的前輩來帶領的時候,蔡惠如適時出現,扮演起父兄的角色,與適時來到日本的林獻堂攜手並肩,成為東京台灣留學生的領導者。
1919年底,在蔡惠如和林獻堂的奔走聯絡下,東京留學的臺籍知識青年,包括較活躍的林呈祿﹑黃呈聰﹑蔡培火﹑鄭松筠﹑彭華英﹑王敏川﹑王鐘麟等等﹐開始組織團體﹐經過幾次調整之後﹐終於在1920年 1月11日成立「新民會」﹐糾集會員一百多人。他們推舉霧峰林家出身的林獻堂為會長。決定三項行動目標:
一﹑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以增進台灣同胞的幸福;
二﹑發行機關刊物﹐以擴大宣傳﹐並聯絡各界互通聲氣;
三﹑圖謀與中國同志接觸之途徑。
第一個目標的具體表現﹐就是「六三法徹廢運動」的推動;第二個目標的具體表現是《台灣青年》雜誌的創辦。
「六三法撤廢運動」﹐顧名思義﹐是要向日政當局要求撤廢對台灣差別待遇的「六三法」。按日本治台的第二年(1896年)﹐由國會通過第63號法律﹐授權台灣總督﹐准其發佈與法律同等權限的行政命令。這是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的根本。但不久﹐大家接納林呈祿的建議﹐認為臺灣原本與日本不同,與其要求撤廢六三法,不如在六三法所認定的臺灣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要求在臺灣設立擁有立法權﹑預算審查權的臺灣議會﹐賦予自治的權利﹐因此﹐運動遂轉向成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年1 月30日﹐一群台灣社會精英首度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設置台灣議會的請願﹐展開長達14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項運動﹐配合著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成為19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台灣的社會運動的主流。
請願的過程﹐首先在全島各地徵求簽署﹐然後推派請願代表準備赴東京請願。行前先舉行餞行活動(集會演說)。請願代表抵達東京時﹐台灣留學生發動迎接﹐並遊行東京市街﹐散發請願傳單﹐表達台灣人的心聲﹐最後到日本帝國議會遞交請願書。其結果當然最後都遭帝國議會駁回。但請願的過程﹐本身即是一種社會教育﹐藉以引起台灣人民及日本人民的注意。在第三次請願時﹐有一位在飛行學校留學的臺籍青年謝文達﹐甚至還駕駛著飛機在東京上空散發傳單﹐相當引起注目。
至於《台灣青年》雜誌的創刊﹐由於新民會會員多為財力有限的留學生﹐創辦刊物談何容易?當時有任俠之風的蔡惠如﹐不顧自己經商失敗的窘境﹐於前往北京之前﹐在東京車站悄悄掏出1500圓交給前來送行的林呈祿說:「這些款項給你們充作創刊之用﹐就算只能發刊一﹑二期﹐也要實行。」蔡惠如這1500圓感動了這些青年人﹐終於催生了《台灣青年》雜誌的創刊。發刊詞中揭櫫發刊的旨趣﹐在於介紹內外文明﹑詳論台灣政治應討論之事﹑爭取台灣的政治自由與文化的啟蒙﹐並謀日華之親善。《台灣青年》創刊於1920年 7月,當初只獲准在日本本土刊行﹐不得在島內發行。然而﹐春風關不住﹐《台灣青年》卻漸漸在島內(包括北師和北醫)的青年學生手中偷偷流傳起來﹐影響了島內的部份知識青年﹐例如當時正在台北師範就讀的一位學生領袖林秋梧﹐便經常將《台灣青年》雜誌帶到學校給同學們偷偷傳閱。《台灣青年》發行18期之後﹐改名為《台灣》繼續發行﹐後來又創刊《台灣民報》﹐繼而改組為《台灣新民報》﹐在島內發行﹐被稱為日治時代唯一的「台灣人民的喉舌」,我們在後面再來介紹它。
總之﹐新民會的出現﹐為1920年代台灣的各項民族運動﹑社會運動起了一個帶頭啟動的作用,自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
台灣文化協會的誕生
1921年 2月﹐由林獻堂所領導的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台灣與東京展開。議會運動刺激了正在台北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的醫師蔣渭水。他是促成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的最關鍵人物。蔣渭水,台灣宜蘭人,出生於日本治台的前四年-1891年。1910年入台北醫學校,在學期間,曾與同學杜聰明、翁俊明計畫,準備帶霍亂菌到北京試圖謀殺袁世凱。雖然這項異想天開的計畫沒有付諸行動,也可以看出學生時代的蔣渭水,對當時中國大陸上的政治已很關心。
這位「北醫」時代曾經表現政治狂熱的醫師﹐在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展開之初,重燃他冷卻一時的「政治熱」﹐開始糾合同志。蔣渭水一方面與林獻堂﹑蔡培火等人「遙為響應」﹐一方面與一些學校裡的知識青年交遊。在星期假日時﹐蔣渭水的醫院﹐經常聚集一些青年學子,其中以「北醫」和「北師」兩校的學生最多。「北醫」即台北醫專,原稱「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北師」即台北師範學校,原名「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在1928年的台北帝國大學創設之前,「北醫」和「北師」是台灣島上最著名的兩所最高學府,網羅了當時台灣島上的秀異青年。有人還曾經把「北醫」和「北師」比喻成台灣的劍橋與牛津。這些青年學生與蔣渭水闊論時局﹐交換心得。
重燃政治熱的蔣渭水﹐與新交的同志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終於有「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蔣渭水曾回憶說:「自獻堂氏歸台﹐在台北開了歡迎會以後﹐新交的同志﹐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諸氏﹐屢次慫恿我出來組織團體﹐並提出他們所做的青年會規則和我研究﹐我考慮了以後﹐以為不做便罷﹐若要做呢﹐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由是考察出來的就是文化協會了。」「台灣人現在有病了……我診斷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痊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
台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10月17日下午 1時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創立大會﹐會員人數1032名﹐當天出席會員300 餘人﹐以北醫﹑北師﹑商工學校﹑工業學校學生佔多數。據日本警察調查報告﹐在1032名會員中﹐學生佔279 名﹐約佔會員總數的10分之 3。當時的青年學生如此關心台灣社會,很值得我們今天許多只知道玩樂的青年學生反省。
台灣文化協會推林獻堂為總理,名詩人林幼春為協理,蔣渭水、蔡培火為專務理事,王敏川、王受祿、賴和、連溫卿、蔡式穀、楊肇嘉等41人為理事,………。
初期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包括有:一、會報發刊;二、設置讀報社,供民眾閱覽;三、舉辦各種講習會;四、開辦夏季學校;五、文化講演會(全島巡迴演講);六、文化話劇運動;七、「美台團」(電影巡迴隊)放映社教電影。
讀報社
「讀報社」是文協啟發民智最重要的據點,由於當時日本政府對所有言論機關予以管控,民眾難以見識真實的報導,況且官方媒體對文協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若非漠視,就是加以扭曲醜化或攻擊。為了突破此一困境,乃創辦《台灣民報》作為報導、批評時政的媒體。之後,《台灣民報》不僅成為「台灣人唯一喉舌」,更是台灣新文學運動萌芽、成長的園地。然而彼時台灣總督府對《台灣民報》打壓極厲,讀者常懷戒心,而且一般民眾恐也無力訂購,所以文協乃在各地設立「讀報社」,提供多種台灣、日本、中國的新聞雜誌或圖書給民眾閱覽,充分發揮消息流通、傳播新知的功能。嗣後,讀報社更成為文化演講、舉辦活動的場所,而成為文協各地的主要據點,發揮相當大的功能。
通俗講習會
殖民地教育通常重視高等教育,以培養統治者的助手,而對於庶民大眾則只施以初等教育,使其愚昧便於統治,日本對台統治即是施行此一愚民教育政策。然民眾知識水準的提升是文化抗日的基石,因此文協便利用舉辦通俗講習會的方式達成對社會大眾啟蒙及社會教育的目的。
講習會舉辦期間長短不一,通常利用晚上時間,地點則大都在台北、台南及彰化等地,類型內容也五花八門,有漢文、歷史、法律、衛生、經濟、文化、科學甚至英文講習都有,講師大都來自文協的重要成員,而民眾反應也非常熱烈,常常「聽眾雲集無立錐之地」(台灣民報語),其盛況可想而知。
然民眾反應愈熱烈,統治者愈害怕,除了出動警察臨場監視騷擾外,更陸續制定各種取締規則嚴加限制。文協的講習會便在日本統治當局高度警戒之下辛苦開展,直到治警事件發生,文協重要幹部被補坐牢才式微,然對於傳播新知、啟迪民眾實已功在不捨了。
夏季學校
1923年10月17日,文化協會召開第三次大會於台南市,議決利用暑假舉辦夏季學校。自翌年(1924年)起連續三年在霧峰舉辦,林獻堂提供霧峰林家萊園充作校舍兼宿舍,男女兼收。先後所開課程,包括有宗教、哲學、論理哲學、台灣通史、憲法、經濟、西洋文明史、科學概論、經濟思想史、中國古文明史、外國事情、衛生、孝道、中國學術概論、社會學、新聞學、人生我觀、星宿講話、資本主義的功過、法的精神、結婚問題、何謂自治.等課程。當時聘請的講師﹐有許多頗具聲望及學養的名士﹐例如林茂生講授其中哲學、論理哲學,西洋文明史的課程﹔連雅堂講授台灣通史﹔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陳炘,擔任經濟學等課程。
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對台灣文化協會夏季學校的開辦,有這樣的評語:「台灣自始至終悠悠半世紀,除卻兩三個教會學校外,完全沒有一所台人辦理的私立學校。可見在當時文協舉辦夏季學校,是含有對台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用行動來表示抗議的意味。」
文化演講
文化協會的另外一項重要活動是巡迴全島的所謂「文化演講」。文化演講頗受民眾的歡迎﹐根據統計﹐1925﹑26兩年中﹐在全島各地所舉辦的演講會的聽眾人數﹐計有23萬多人。這個數目在當時約300萬的台灣人口當中﹐比例應不算少數。
當時這種從事演講的人稱為「辯士」。日本警察當局對於文化協會的辯士的演講內容極不放心,每場演講會都派有警察在現場監聽,遇有「辯士」演講的內容過於激烈,有過於批判日政當局,煽動民眾反日情緒時,警察往往會發出「辯士中止」的命令。
台灣文化協會會員遍及全島,他們在全島各地的活動,與當時正展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揮著相輔相成的作用,參與的人員幾乎重疊。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帶動議會請願運動進入高潮。
治警事件
1923年2 月,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進行第三次請願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決定組織一個常設團體﹐以做長期抗爭﹐遂有「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產生。不料這個組織﹐違反了日本於同年初頒布的「治安警察法」﹐於是日本當局於12月16日在全島各地對議會運動的活躍份子進行一場大逮捕﹐全島各地的會員及相關人士紛紛受到日警當局的傳訊﹑搜宅﹑調查﹑跟蹤﹐一時風聲鶴唳﹐這就是日據時代著名的「治警事件」。這次的整肅行動中﹐被扣押者41人﹐被搜查及傳訊者11人﹐被搜查者12人﹐被傳訊者35人﹐一共99人﹐幾乎全是文化協會的重要幹部,最後計有18人被起訴。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初審判決時﹐被告全部獲判無罪。第一審的日本法官崛田真猿在判決中說:「….我相信被告所說的話﹐是三百萬臺灣島民向日本帝國所要說的。在尊重彼等人格﹐並為日臺人之間的融合起見﹐非故意無視臺灣的施政方針﹐蓋以法規為根據而公平審理者也。」但後來因檢察官三好一八不服上訴﹐二審時﹐有12人被叛徒刑﹐最高刑期是蔣渭水和蔡培火被判四個月﹐次為蔡惠如﹑林呈祿﹑林幼春﹑陳逢源等人的三個月….。
這些社會精英入監時﹐民眾夾道歡送﹐場面感人。例如蔡惠如從清水家中到臺中入監﹐當他從火車站一出來﹐沿街民眾自動燃放鞭炮﹐高呼萬歲﹐臺中警察署長騎馬(鎮暴馬?)揚鞭驅趕民眾﹐但民眾散了又聚﹐一直跟到監獄門口。蔡惠如─這位被譽為「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在獄中寫下了這闕感人的獄中詞<意難忘>:
芳草連空﹐又千絲萬縷﹐
一路垂楊千愁離故里。
壯氣入樊籠﹐
清水驛﹐滿人叢﹐握別在臺中。
老輩青年齊見送﹐感慰無窮。
山高水遠情長﹐
喜民心漸醒﹐痛苦何妨。
松筠堅節操﹐鐵石鑄心腸。
居虎口﹐自雍容﹐眠食亦如常。
記得當年文信國﹐十古名揚。
這些入獄的精英﹐幾乎每個人都能詩擅文﹐而且都留有獄中創作﹐不勝枚舉。例如被譽為日治時代台灣的三大詩人之一的林幼春(南強)﹐有許多獄中詩作﹐我們試舉其中這首題為〈獄中寄內〉的七言律詩來欣賞:
板床敗薦尚能詩﹐豈復牛衣對泣時。
到底自稱強項漢﹐不妨斷送老頭皮。
夢因眠少常嫌短﹐寒入春深卻易支。
昨夜將身化明月﹐隔天分照玉梅枝。
善寫歌詞的蔡培火﹐在獄中填了一首<臺灣自治歌>﹐我們試以閩南語朗讀﹐體會一下他們當時為臺灣奮鬥的心情:
蓬萊美島真可愛﹐祖先基業在﹐
田園阮開樹阮栽﹐勞苦代過代。
著理解﹐著理解﹐
阮是開拓者﹐不是戇奴才。
臺灣全島快自治﹐
公事阮掌才應該。
治警事件使得台灣民氣更加旺盛。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服刑期滿出獄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繼續推動﹐配合著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啟蒙運動,使得台灣的民族運動﹑社會運動﹐逐漸進入高潮。
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演講活動,在全島各地如火如荼展開,引起日本警察當局相當的注意。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當局的報告:「大正14年(1925年)可以說是文化協會舉開講演會的狂熱時代 ﹐地方會員﹐凡有機會即邀請幹部去開演講會。發動民眾藉口歡迎﹐沿途燃放爆竹﹐高呼口號﹐作一種示威運動﹐舉行旁若無人的盛大歡迎會﹐以張聲勢。幹部也儼然以志士自居﹐睥睨一切﹐徒以挑撥民族的反抗心為能事﹐釀成普遍的反母國(日本)的風氣。尤其是每次介入地方問題或農民爭議﹐助長糾紛﹐以收攬民心﹐如遇取締﹐則展開執拗的演講戰與示威運動﹐以示反抗。這運動實開本島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的先河。」
電影巡迴隊-美台團
台灣文化協會從事啟蒙工作﹐除了以巡迴演講為主要方式之外,為了讓鄉間民眾更有效吸收新知,激發民族意識,文化協會於是進而成立電影巡迴放映隊。當時文化協會的專務理事蔡培火 ﹐尤其重視電影對大眾的教育功能。1925年秋﹐從東京購買社會教育影片十數卷﹐及電影放映機一部﹐設立「活動寫真班」(也就是電影班)﹐名叫「美台團」﹐訓練具有教育經驗的青年志士三人﹐一人專管機器﹐二人分任辯士(解說員),當時的電影還是默片,所以需要解說員從旁解說。林秋梧﹑盧丙丁即是當時美台團裡面著名的辯士。「美台團」的電影隊最初只有一隊﹐巡迴放映於當時的台北州及台中州各地﹐頗得各地民眾歡迎﹐遂於1926年9 月起﹐又組織第二隊電影隊﹐巡迴於南部的農村小鄉鎮之間。在當時資訊媒體尚不發達的時代﹐台灣文化協會巡迴在鄉間的電影隊﹐受到民間相當熱烈的歡迎。文協電影隊在各地巡迴放映之前,都事先安排訂有日程表。但往往因為觀眾熱烈,應地方要求多留映了數天,以致於原訂的日程常常拖延下去,令下一站的民眾迫不及待。
「美台團」的催生者蔡培火﹐為美台團作一團歌﹐歌詞如下(以福佬話發音):
美台團﹐愛台灣﹐愛伊風好日也好﹐愛伊百姓品格高。
長青島﹐美麗村﹐海闊山又昂(音權)﹐大家請認真﹐生活著美滿。
美台團﹐愛台灣﹐愛伊水稻雙冬割﹐愛伊百姓攏快活。
長青島﹐美麗村﹐海闊山又昂(音權)﹐大家請認真﹐生活就美滿。
美台團﹐愛台灣﹐愛伊花木透年開(音虧)愛伊百姓過日美(音水)。
長青島﹐美麗村﹐海闊山又昂(音權)﹐大家請認真﹐生活著美滿。
美台團每次開映之前﹐團員必合唱此歌一次﹐後來觀眾都聽熟了﹐也就自然與團員一齊高聲合唱起來﹐聲浪雷動﹐充分流露了一番同胞相愛互勉的氣氛﹐深印人心。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至此可說是進入新的境界。
文化劇運動
為了要改革傳統文化中的陋習弊病,涵養民眾高尚的文化氣息,台灣文化協會在1923年於台南召開總會時,就已決議開辦新事業,除了前面介紹的電影隊美台團之外,就是創立文化劇團。這個新劇運動的興起,除了革除舊戲曲的封建內容之外,大都含有諷刺社會制度或激發民族意識的作用。1920年代中期,遍佈全島的文化協會會員,在各地紛紛成立新劇社團,例如-彰化鼎新社、草屯炎峰青年演劇團、新竹新光社、台北星光演劇研究會、霧峰一新會、台南文化劇團、安平劇團、宜蘭民烽劇團、北港民生社、台北博愛協會、麗明演戲協會…..。
台灣民報
我們在前面談過,1920年初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成立的「新民會」﹐在蔡惠如﹑林獻堂的支持下﹐創刊《台灣青年》雜誌﹐後改名《台灣》﹐但其發行量終究有限。到了1923年﹐民族運動的有志之士有感於台灣人需要一個屬於台灣人的言論機關﹐因此 ﹐繼而創刊《台灣民報》。
1923年(大正12年) 4月15日﹐《台灣民報》在東京創刊﹐原先是半月刊﹐後改為旬刊。1925年7月12日起﹐再改為週刊(每星期日出刊)﹐報份已達1萬份。到了1927年8月1日起﹐開始遷入台灣發行﹐仍以週刊出現。1930年(昭和5年)3月﹐為了進一步替發 行日刊做準備﹐乃增資改組﹐並易名為《台灣新民報》。到了1932年4月15日正式獲准發行日刊﹐廣受台灣人喜愛。
《台灣民報》發刊詞說:「處在今日的台灣社會﹐慾望平等﹑要求生存﹐實非趕緊創設民眾的言論機關﹐以助社會教育﹐並喚醒民心不可。」這個台灣民眾的言論機關﹐扮演著批評時政﹑傳遞民瘼﹑介紹新知﹑提昇文化的角色。自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來的台灣各種政治﹑社會運動﹐包括文化啟蒙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無不受到《台灣民報》的熱烈支持與鼓吹。《台灣民報》可說是橫跨1920年代到30年代的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機關報。所以《台灣民報》被譽為「台灣人唯一言論機關」、「台灣人唯一的喉舌」。雖然用「唯一」來形容﹐或許稍嫌專斷﹐因為尚有許多小型刊物仍發出台灣人的心聲﹐然其影響力﹐畢竟難與《台灣民報》相匹敵。
所以﹐要瞭解1920﹑30年代台灣人的民族運動﹑社會運動..﹐《台灣民報》是絕對不能忽略的重要史料。
《台灣民報》「除做台灣人的喉舌﹐呼籲訴苦﹐對總督府的惡政加以指責批難﹐對民間日人的歧視曲解予以糾正外﹐對台灣人的思想﹐文化的啟蒙也有甚大的幫助」(葉榮鐘語)﹐《台灣民報》對新知識﹑新思想的介紹﹐反應了那個世代台灣知識份子的世界觀﹐透過《台灣民報》﹐20年代的台灣人早就對羅素﹑胡適﹑魯迅…不陌生。
《台灣民報》也經常報導當時中國的政情﹐中國的軍閥如何混戰﹐蔣介石與汪精衛如何鬥法..。所以《台灣民報》也提供了中國近現代史的珍貴史料。
更重要的是,《台灣民報》對新文藝的鼓吹﹐是台灣新文學創作的重要園地﹐促進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許多日治時代的重要作家,都在《台灣民報》發表文章,幾次重要的文學論戰,也在《台灣民報》引燃。
這樣做為台灣人喉舌的《台灣民報》﹐必然引起日政當局的注目﹐壓力也隨之而來﹐日本人透過新聞檢查制度﹐來箝制《台灣民報》。今天我們翻閱這份台灣報業史上的重要報紙﹐可以發現許多因為遭禁止刊登而翻成「鉛屁股」的無字文章﹐裡面雖黑烏一片﹐認不出半個字﹐卻寫滿了對專制統治者的血淚控訴。誠如1930年7 月《台灣新民報》創刊十週年時﹐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在新民報上發表的祝賀專文所說的:(原作日文)
「..從誕生以來既遭遇外界種種強烈的壓迫,並承受內部的分化,歷經十年,終而確立地位的新民報,實在是從惡戰苦鬥中過來的。在台灣新民報十週年的此時,自身所傳達出的,就是他確立了台灣人言論權的歷史。從它與社會的互動中,留下了台灣各種解放運動的血與淚的可貴紀錄。基於上述這些意義,吾人對過去民報及諸同志的努力奮鬥,應表最大的敬意。」
學生運動
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緣自於一群與蔣渭水來往的青年學生。文化協會成立後,參加的成員中,學生比例很高。文化協會所舉辦的文化演講、電影巡迴、文化劇等活動,參與最力的,也是青年學生。因此,文化協會對青年學生的影響也最深。
1922年2月3日,距離台灣文化協會創立不到四個月,台北師範學校爆發了抗日學潮,起因於日本警察與學生為了交通紀律問題產生的爭執,日警到校訓誡學生,引發三百多名台灣學生向日警抗議,投擲石塊,前來支援的警察署長向學生拔刀恐嚇,引起更大抗議。事後,有45名學生遭警方逮捕,最後雖獲不起訴,但其中15名學生遭校方退學,他們都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退學生當中的林秋梧,就是後來擔任文化協會電影巡迴隊美台團的一位辯士。經過這次學潮,日本當局認為這是學生受台灣文化協會煽動的影響,校方因此強迫學生退出文化協會。
但這次學潮之後,一連串的學潮接踵而來-1924年11月18日台北師範又發生第二次學潮;1925年4月3日,有台南師範學校的學生罷課事件;1926年10月25日有台北商工學校學生罷課;1927年5月有台中一中罷課;1928年3月23日有台南師範學校罷課;1928年11月 9日又有台中師範罷課,這一連串的學潮,都起因於日本當局對台籍學生的差別待遇。這些學生運動,都是1920年代台灣的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一環,與文化協會息息相關。
農工運動
台灣文化協會可以說是1920年代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大本營﹐也是許多社運團體的「母體」。經由文化協會的啟蒙﹐不僅激勵了1920年代多起青年學生運動﹔更由於文協走向農村與民間﹐也替台灣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開啟先河。
1925年10月﹐彰化二林一帶的蔗農因為向製糖會社提出蔗農權益要求﹐與日警衝突﹐釀成集體遭受逮捕﹑判刑的「二林事件」,事件的首腦李應章醫師,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幹部。因為有「二林事件」的激盪,台灣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團體「台灣農民組合」遂於隔年(1926年)的 6月28日成立。領導幹部幾乎都是文化協會的會員。
分道揚鑣
因為農運﹑工運的崛起﹐文化協會的參與份子中﹐左翼青年日增。1927年 1月﹐台灣文化協會開會員大會﹐連溫卿﹑王敏川等左翼新勢力掌握了文化協會的主導權﹐取代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文協舊首腦﹐台灣文化協會內部發生左右分裂。林獻堂﹑蔣渭水等舊幹部乃退出文化協會﹐另組團體﹐遂有台灣民眾黨的誕生。分裂後的「新文協」﹐走向農工運動的道路﹐主導1920年代後半期台灣的左翼運動。
身份認同的檢討-代結語
在紀念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八十週年的今天,我們緬懷前人的努力,我們以虔敬的心情,細讀台灣歷史上這一頁璀璨而光榮的記錄。那一批熱血沸騰的台灣知識青年,在異民族的殖民統治下,目睹社會的不公、文化的頹喪,同胞的困境,紛紛挺身而出,他們走向大街,踏入小巷,從事街頭演講,放映電影,他們敢於向強權抗爭,為社會探病,替同胞代言,為喚醒民眾而呼號,為台灣人的「知識的營養不良症」注下維他命。
不過,撫今追昔,我們除了感念前人的努力之外,也要從歷史中做一些反省與檢討。
當年從事文化啟蒙運動與民族運動的前輩們,為了與日本進行民族抗爭,部分領導者在身份認同上仍以傳統的「漢民族」「炎黃子孫」或「中華民族」等符號做為區隔台灣人與日本人的認同指標。例如:
被譽為「台灣的民族運動的鋪路人」的蔡惠如,在《台灣民報》創刊號上說:「台灣的兄弟不懂漢文,我所以滾下珠淚兒來咧。這個原故,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台灣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來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為什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
蔣渭水在他所寫的<臨床講義>中,對「患者:台灣」的敘述是:「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遺傳: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
畢生拒絕講日本話的林獻堂,曾因為稱中國為「祖國」而遭日本浪人毆打,他作詩還夢想著「祖國我欲乘風歸」。
足見,這種訴諸血緣、種族的認同,是當時台灣文化協會的主流前輩們用以區別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重要標準。因此「漢民族」成為重要的認同符號。而「中華民族」這個甫隨著清末民初中國政局的丕變而被建構出來的政治符號,也立刻被當時蔣渭水等人吸收採用。在他們的觀念中,「漢民族」、「中華民族」、「黃帝子孫」等名詞,幾乎都是同義詞。儘管論者多以為日本時代已逐漸形成「台灣意識」,甚至有「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口號,然而其「台灣意識」是相對於「日本意識」而言,「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另一面意義是在表示「台灣不是日本人的台灣」。因此,當時的台灣意識,不但未排斥「中國意識」,反而有以「中國意識」為內涵。
對於這一派訴諸「黃帝子孫」、「漢民族」、「中華民族」的運動幹部,研究台灣史的史明先生曾有如下的評語:「現實存在著的台灣.台灣人,與現實的中國.中國人雖屬於同一種族,但二者在社會上、意識上已成為不同範疇的二個民族集團….(中略)….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是所謂「民族派」的前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要幹部,不但不把這點認識清楚,反把現實的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大眾(多數者)的心理動向(台灣人意識),跟他們自己在腦筋裡所幻想的「祖國中國」、「中國的台灣」等抽像觀念混淆在一起,結果,不知不覺之間,卻以「祖國中國」的幻想為基本觀念來從事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所領導的解放運動乃不可能直截了當的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只是心理上在「祖國中國」的觀念世界打圈子。」
史明的評語,提供了後人一些反思的途徑。如果以林獻堂先生在後來橫跨兩個時代的處境來對照,我們或許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說明-日治時代領導台灣民族運動達二十多年的林獻堂,儘管那樣一廂情願地謳歌「祖國我欲乘風歸」。然而,終戰之後,他夢寐以求的「祖國」來臨後,林獻堂不僅備受排擠冷落,許多同志朋友在二二八大屠殺中受害,繼而他也在「土地改革」的美麗招牌下幾乎被剷除根柢,終於失望地離開台灣,流寓日本,最後客死異鄉,留下這樣無奈的詩句-「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底事異鄉常作客?恐遭浩劫未歸田。」
緬懷過去,展望將來,我們應該發揚前人的奮鬥精神,也應該記取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