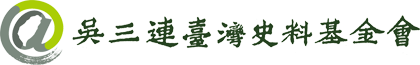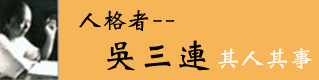陋巷、水邊、溫情──莫渝專訪
 |
時 間:1999年8月23日、1999年11月29日 地 點:台北縣板橋市莫渝宅 |
莊紫蓉1
首先請你談談出生的地方,以及童年生活的環境,好嗎?
莫 渝1
我祖父本來在中港溪旁邊有田地。日治時代竹南中港地區很熱鬧,大船都可以開到港邊,再往裡面是個繁榮的市區,中港算是竹南較早發展的地區。小時候,我聽人家說有鯨魚擱淺在中港溪出海口,很多人跑去看。似乎也出過一些意外,漲潮時,有人來不及跑,就被淹死了。
我祖父那一代,家境還不錯,聽說我大姑姑出嫁時的陪嫁,有樓房和田園。我父親是我祖父最小的孩子,1917年出生,成年時 ,家道已經中落,就帶著3個孩子到南投的竹山學駕駛,也就是學開卡車(拖拉庫)技術。當時駕駛必須接受嚴格訓練,就像鍾理和到中國東北的汽車學校學駕駛一樣。後來,又搬回竹南。戰爭期間,父親曾在日本陸軍部擔任司機(運將、運轉手)。我就是在竹南出生的。
我們在竹南住的房子很小,是租的。記得住家附近有一條河溝,我常常和鄰居的小孩子在河邊與水中玩。河的上游有竹林、蘆竹,雜草叢生,我們曾經去採蘆葦,做成蘆笛吹著玩。童年,河邊的生活,對河流上游,有一種陌生、好奇與嚮往的感覺。其實,那裡離開住家大約1、2公里而已,但是很多雜草,很荒僻,河裡又常有水蛇,河兩岸沒有河堤,都是樹林、灌木叢。河面寬約十公尺,大人也在那裡洗衣服。
記得那時,有一個年紀較大的玩伴,他會帶著我們做蘆笛、做彈弓、爬樹、游泳等等,好像「囝仔頭王」一樣。我在八○年代翻譯一篇南斯拉夫小說家柯爾塞維克的<赤腳與天空>,裡面有類似的角色和童年玩伴。
莊紫蓉2
小時候,你對那個囝仔頭王有沒有很崇拜,或是追隨他做什麼事?
莫 渝2
沒有這樣的感覺,只覺得他會帶我們去玩。他大概是輟學生(當時沒有這個名詞),家庭狀況不是很好,他父親沒有固定工作,有時到山裡面打獵,或是釣魚,有時打打零工。
我們家附近一帶是平地,最常玩耍的地方就是那條河溝,覺得很親切。遠方有山,但是,我沒有什麼冒險精神,也沒想跑到山上去探險。所以對山就覺得比較遙遠而神祕。
當時,我祖父回到老家(地名:港仔墘)去住,但是,他已經沒有產業了。當地大人或長輩都認識他,提供一幢日本人留下來的簡陋房子給他,我祖父母和我大伯父就住那裡。我大伯父也學會開車,不過他卻一直沒有做卡車司機的工作,僅靠幫村人割稻或做零工維生。逢年過節,我們會走2個小時的路到祖父家。有幾年清明節,我曾經和祖父挑著前一天準備好的祭品、素菜等去掃墓。那一段路,都是石子路,路兩邊高大的木麻黃,給我的印象很深,沿途,聽到颯颯的風聲,有股奇妙的感受。
竹南近鄰是頭份鎮,從竹南到頭份有柏油路,我三、四年級時有個同學轉學到頭份,假日,偶而我們會約幾位同學,走那條路去找他。那段路的路面相當好,路兩旁的油加利樹也相當高大,夏天,整條路上,蟬高聲鳴叫。八○年代初,我在法國時,看到成排挺拔的白楊樹,讓我直覺地聯想起童年看到的那些油加利樹。我曾經寫一篇文章列舉、比較這兩種俊偉高大的喬木。二、三十年前,因為馬路拓寬,油加利樹被砍了不少,令人惋惜。
莊紫蓉3
家人當中,你跟誰比較親近?
莫 渝3
都差不多。我姊姊小學畢業後,就到工廠工作,她對弟妹很照顧,幾個兄弟姊妹都相處得很好。
當時整個社會的經濟不很好,小孩子的玩具大都是自己想辦法做的,比方把酒瓶蓋打平,用繩子貫穿過去,兩端繩子一拉,就會打轉,也可以拿來當紙牌玩。將油加利樹的果實摘下來剖成兩半,去掉裡面的碎鬚,用姆指和中(食)指讓它旋轉,好像一個小陀螺。互彈龍眼子是夏天的玩法,把吃過龍眼的核洗乾淨,收集起來,每個孩子都用個罐子來裝這些龍眼子,比賽結束,各自收藏,大都藏在床下的一個角落。此外,踢罐頭罐(俗稱:銅管仔)、捉迷藏,秋末或冬天的焢窯、打田土仗(互扔休耕時田里的乾土塊)等,都是我們共同的遊戲。所以,物質生活不談,我的童年是滿快樂的。
有些心理學家認為,在大自然環境下成長的小孩,心智上會比較活潑、快樂。
莊紫蓉4
你的童年應該也算是在大自然環境成長了?!
莫 渝4
竹南是一個小市鎮,沒有廣大原野的開闊視野,只是住家附近有小河流、有雜草,感覺上是跟大自然很親近的。那時台灣社會還比較純樸,物慾的追求不強,購買慾不高,小孩子之間很少互相比較什麼。
莊紫蓉5
你有一首詩<背影>,是寫你的父親,讓我印象很深。是不是你跟父親比較親近?
莫 渝5
我倒沒有感覺跟父親比較親近,不過,有一次,父親帶我到街上看電影,那次的經驗,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戰後,我父親是貨車司機,主要是運煤。頭份再往山裡去的南莊產煤,煤礦公司就僱用一批司機將開採出來的煤炭運到火車站邊的礦場,再由火車轉運南北各地。我家就在竹南火車站附近。現在煤礦業已經沒落了,這些火車站旁邊的礦場都改建成樓房。桓夫有一首詩<苦力>,描寫四O年代初的勞工,在五、六○年代,也有受雇於礦場或工廠倉庫的同類型的搬運工人。我讀照南國小時,從家裡到學校要走四、五十分鐘的路,會經過台糖的甘蔗林,經過平交道、紙廠、磚窯,常看到工人在搬貨物,或是將火車車箱、車皮推到轉掣處,更換軌道。小時候,看過這樣的勞動工人,對工人的印象滿深刻的,汗流浹背的,腰間繫條毛巾,不時有笑語傳出,當時,我並不覺得他們有什麼苦的。
我父親是貨車司機,有一天晚上,他用卡車,載一群人去新竹看電影。記得那次的電影是日本片《柳生英雄傳》,描述幕府時代的武士。「搶巴拉」(武士道、劍術)這樣的語詞也能朗朗上口。
| 莫渝先生 陳秀喜作品討論會 攝於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1997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6
你父親對你們的管教會不會很嚴格?對你有什麼期待?
莫 渝6
我讀書的成績還好,又是長子,受到的照顧比較好,父親沒有苛責過我,倒是母親曾經打過我一次。那是因為我跟媽媽說需要糨糊,母親就用稀飯熬成糨糊給我,後來,她從同學那裡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認為我說謊,就把我綁吊起來打,。
當時家庭經濟不是很好,有時會向米店賒米,沒有菜餚就用豬油、醬油拌飯吃,小孩子也吃得很香。在那個年代,大家的經濟都不好,所以我們也不會感覺特別貧窮。
那時,學生使用書包的並不多,多半是用包袱巾包書。我上小學時,父母特別買了一個大書包給我,上學也有鞋子可以穿,不像有些同學打赤腳。當然有時我也會打赤腳,因為到附近的田地去玩,赤腳比較方便。
莊紫蓉7
小學時有沒有老師對你比較特別的?
莫 渝7
記得小學二年級時,我不知道為什麼事情哭,那位女老師安慰我,讓我感覺老師好像特別疼我。
三年級時換了一個男老師,「九九乘法表」我一直背不起來,被老師打得滿嚴重的。四年級之後,一直都有被老師寵愛的感覺。
莊紫蓉8
被老師打的心情如何?被打以後有沒有把乘法表背起來?
莫 渝8
我覺得被打是應該的,自己不會就該被打啊,這是當時的想法。也許我開竅比較慢,剛開始學習新事物比較困難。後來,大家都會背了,我也背起來了。
四、五年級時,記憶力較強,看了不少中國民族英雄的故事,對於歷史漸漸發生濃厚的興趣。有一次,父親要我向老師借有台灣人物介紹的雜誌給他看,好像他也很想瞭解有關台灣早期的事情。
莊紫蓉9
那時,你就很喜歡看書了?
莫 渝9
記得當時,學校圖書室(大辦公室的一角落櫃子)有一本《新少年世界地理》,好像是《中央日報社》印的,介紹世界各國的人文。此外,還有整套中國革命烈士小冊子,如秋瑾、黃興、史可法等。那些書,我都很喜歡看。閱讀這些清末民初的人物傳記,使我瞭解那段令人熱血澎湃的歷史,因而,希望自己也能投入到那樣的熔爐裡。
五、六年級時,讀到一篇<憑弔趙伯先烈士>的課文,文詞慷慨激昂,給我印象深刻,感覺激勵性滿強的。記得文章開頭是「在鎮江南郊,一個蒼鬱的竹林裡,……」,後來,我知道那是憑弔三二九之役犧牲的趙聲洞的一篇文章。四年級時的一篇課文<米海>,我也還留有印象。以後,我查出那是葛賢寧《霜葉》裡的一篇文章。<米海>寫中共佔領中國大陸之後,把江南的米運到北方,一群江南的老鼠,發現江南都沒有米了,就到處尋找,最後,在東北的佳木斯發現一個大米倉。這是一篇反共散文。
那時,小學畢業要繼續升學的,必須參加初中入學考試,所以有所謂的惡補。惡補時在國語試卷閱讀測驗會讀到好多不錯的文章,例如<思母>這篇文章就讓我印象深刻,後來,我才曉得這是日本童話作家吉田絃二郎的作品。
莊紫蓉10
你讀過這些文章,受到感動,有沒有想到自己也寫寫看?
莫 渝10
有人在小學時就開始寫文章、投稿,我倒是沒有這種念頭,那時寫文章的機會也不多,家裡周遭沒有文學書刊,學校的作文課也沒什麼特殊表現。有一次,寫下雨的文章,我抄了幾句看過的有關文詞,被隔壁班的老師指出。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刺激,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寫文章,更不會想到要當一個作家了。
莊紫蓉11
你小時候有沒有想到長大要做什麼?
莫 渝11
小學的老師教學很認真,我曾經想,以後就當個老師也不錯。不過,只是這麼想想,也不是很堅定的非做不可。
小學畢業之後,就到新竹縣立第一中學(今改為建華國中)讀書,那是我就讀的照南國小第一次有人到新竹讀書。
到新竹讀書,每天要先坐約二、三十分鐘的火車到新竹火車站,再走四、五十分鐘的路到學校,學校位在十八尖山下,鄰近為新竹二女中、新竹中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從一個小地方到一個大城市,視野開闊了。我們學校有初中和高中部,運動場很大,有些活動,譬如校外的台電棒球隊等常常會在學校比賽。上下學搭車或途中,會跟外校及高中部的學生混在一起,言行上、心智上都得到不少啟發。
| 莫渝先生 李敏勇「心的奏鳴曲」演奏,吟詩 攝於二二八紀念館 1999.05.16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竹南和新竹雖然距離不是很遠,但是要坐車、走路,有那麼一點離鄉背井的感覺,也有一些些出外人的味道。在這種心情之下,讀到許地山的<落花生>,激起了我對家庭、親情的感受力,那樣的抒情印象一直留存著。這時,開始購買課外讀物,常到新竹市區的書店、舊書攤看書、買書,《當代中國作家選集》(小說、散文和詩選集)、《海燕集》等等都是在那裡買的,也從《野風》誌,接觸了新詩。我的家庭環境週遭,很少能夠看到課外書,有同學已經在週記上抄寫唐詩三雜百首了,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唐詩,直到在書攤買書、看書,才逐漸認識中國古典詩詞。對李後主從帝王到亡國的詩詞,「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的心境變化,也是在《野風》雜誌上讀到的。
因為通學的關係,認識了幾個學長,他們會照顧我,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一些東西。
莊紫蓉12
在新竹,除了舊書店,還有沒有到什麼地方逛逛?
莫 渝12
有啊,街上、城門一帶都會去逛逛,後來,我用過「迎曦」這個筆名,就是取自新竹東城門城樓的名稱。有迎接第一道曙光之意。
莊紫蓉13
你到新竹讀書,環境上、文學上都開拓了視野,又得到幾位年長的朋友的照顧和啟發──
莫 渝13
那時,在學校圖書館借過泰山和福爾福斯的書。另外,初中一年級暑假,在祖父的住處找到一些線裝書,如《東周列國志》,從這本書,我讀到田單、孫臏、龐涓等歷史人物的故事;從《岳傳》我讀到了岳飛在風波亭被斬的故事。三年級春假,沒有參加畢業旅行,也是在祖父那裡看了《火燒凌煙閣》,是朱元璋起義到登基的故事,小說裡的每個人物都是下凡的天上星宿,陳友諒、張士誠、常遇春、胡大海等等都是。故事結尾是火燒凌煙閣。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後,過去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大將,心裡認為皇帝跟自己就像親兄弟一樣,言行上難免有些隨便,甚至囂張。有人向朱元璋建議蓋一座閣樓,完工之後,就在那裡宴請諸位大將、大臣,表面上做為慶功,暗地偷埋火藥,把樓閣及功臣一併燒燬。先前,劉伯溫已經決定請辭離開宮廷,元帥徐達向他請教如何自處,劉伯溫就告訴他要隨時緊跟在朱元璋身邊。慶功宴那天,大家高興地飲酒作樂,不久,朱元璋表示有事要先離開,徐達想起了劉伯溫的話,就跟著朱元璋離開了。他們離開不久,凌煙閣就發生大火,那批幫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們就這樣身葬火窟,被清除了。
這故事給我的印象很深,這種做法太殘忍了。1982年我在法國時,遇到幾個台灣的朋友,那一年春假,我們四位一起到阿爾卑斯山、法國南部去玩。有幾天,在尼斯附近一家汽車旅館留宿,晚上,和其中一位閒聊時,談到美麗島事件,我對黃信介等涉案的幾位是很同情的。我說彼此是兄弟,是同胞,為什麼要有殘殺呢?順便談起火燒凌煙閣的故事,那位朋友順口冒出:「你為什麼要對人這麼溫情?」
我想,溫情是我寫作的原動力吧!
莊紫蓉14
你本身的性格是溫情的嗎?或是環境造成的?
莫 渝14
或許是個性本身就有這樣的傾向,想到火燒凌煙閣這種做法,就覺得殘忍、不該,像朱元璋那樣把過去幫他打天下的人一筆勾消,我是沒辦法認同、接受的。我寫《笠下的一群》就是抱著同樣的心情來寫的,既然是同伴,「笠」的每一個成員都要一視同仁,不能長期只注意到某幾位,如果有能力的話,也應該凸顯所謂邊緣者的努力。
再講回新竹讀中學時,那時,有幾位新竹本地的同學跟我很要好,畢業以後,彼此分散,就沒有再連絡了。畢業時,有個同學送我一本《文心雕龍》,那是一本我到現在都還看不懂的書,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送那本書給我,還題了字:願玄圃積玉,香象渡河。《文心雕龍》在我的文學歷程只是這麼擦身而過,從來沒有好好去讀它。
莊紫蓉15
你那個同學送你《文心雕龍》,雖然那本書似乎對你沒有產生什麼作用,但是,他送你書這件事本身說不定對你造成一些影響。重要的是他的友情,其次是他很看重你,我想至少這兩點多少影響到你,讓你更有信心。
莫 渝15
我也不太清楚。
當時我們還有一個同學,家住新竹街上,開糕餅店,每天都穿著熨得畢挺的制服,感覺他是很受照顧的孩子。我跟這個同學並不熟悉,但是他也給我留下了印象。
莊紫蓉16
聽你談到小學、中學的情形,好像你交往的朋友年紀都比你大,會照顧你,你似乎比較少跟年紀比你小的交朋友,是嗎?
莫 渝16
好像是這樣,也許是沒有年紀比我小的人來接近我,我也就無法照顧他們了。
初中時,我的學業成績還不錯,父親在礦場工作,算是礦工,我得過兩、三次礦工獎學金,好像是六百元,父親給我五十元。我就想用這筆錢改善家庭經濟,去買愛國獎券(當時一張獎券5元),結果落空了,一、二次之後,我就不再對獎券抱有希望。
中學讀了中國近代史,心中產生一股報國的熱血,那時,我們家庭經濟不好,幾個孩子都在讀書,因此初中畢業時,有一度想考軍校。我把這種想法跟小學的老師商談,他很反對。
初中畢業,如果成績好,可以直升學校高中部。能夠直升的同學都是功課好的,他們多半參加高中聯考,去讀新竹中學。剛好那一年,師專五年制首屆開始招生,由台北、台中、台南三所學校聯合招生,我就報名參加師專聯招。報考前,我跟父母商量,徵得他們的同意,也跟我姊姊有個約定──我考上師專,她買一隻口琴給我。結果我考上了,也得到了一隻口琴。
我會去考師專,當然家庭經濟是個因素,那時新竹師範入學試要考音樂,比較困難。我表哥就讀新竹師範時,我跟他有接觸,記得他送我一本 《勵志文粹》 的書。
講到這裡,我想起小學四年級暑假,在祖父那裡,認識了一個比我年長的學生,借給我一本有關民族精神和生活教育的書,用一個故事說明每一種道德行為。其中有一篇節約的故事,敘述一個廟祝,把有錢人家洗米流失的米粒,收集儲存起來,荒年時,再拿出來救濟。那本書大概是小學「生活與倫理」或是中學「公民與道德」的補助教材。
莊紫蓉17
考上師專之後,你就到台中了,那時,不必通學,是住學校宿舍吧?
莫 渝17
對。學校宿舍是平房,一個房間兩排榻榻米的通鋪,一排好像八個人(八席榻榻米)。當時一個班級四十多個學生,總共四個班級,所有的學生都住宿舍。學校是在台中市西區,剛好在民生、民權、五權等幾條大馬路中間,所以,有時我稱它為「四方城」,距離台中火車站約20分鐘腳程,現在改為師範學院。我就讀時學校就有遷校計畫,說是要遷到台中北屯區大坑,如今過了三十幾年了,還是原地不動,只是教室校舍翻新。
學校正門就是一棟古老的三樓教室,呂赫若(當時不知道有此人)以前讀過的教室還在。我那首詩<夜寒聽簷滴>裡所寫的「挨靠廊柱」,就是師專宿舍的廊柱、屋簷的留存印象,寫那首詩時,距離在校時,已隔了十幾年之後了。
莊紫蓉18
師專五年也是很長,學校所學的有什麼較為有趣的科目?
莫 渝18
主要有語文和教育的科目,教育方面的科目,我讀得不好,不管是教育概論、教育心裡學,或是教育統計學,都感覺很陌生不容易接受。最主要的,可能是因為不再有升學壓力,對學校功課不很在意,常常看文學的書,又認識了幾位文藝朋友,如余成楠、陳恆嘉等,跟文學的關係更加密切。當時,學校有一個社團刊物《蘭心詩刊》,我在第二期介紹鄭愁予的詩,第三期介紹桓夫、趙天儀等以雨為主題的作品。那時,是 1965年末和 1966年初,我已經和趙天儀他們有所接觸了,就希望透過這樣的介紹,讓大家有一個參考、學習的方向。
莊紫蓉19
那時,你的同學或詩刊的同伴認識台灣作家嗎?
莫 渝19
我想,那時候,大家對台灣作家或詩人是不太清楚的,至少不像我有這樣的接觸。這本刊物發行了三期,也在《民聲日報》闢一個詩社專欄,供我們發表。三年級時,我用筆名莫渝發表了<那呢喃的夜──遙念慈母>這首詩。
| 莫渝與巫永福先生 於陳秀喜詩獎頒獎典禮 1997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20
那時,你寫詩、發表詩,這些文學活動,家人知道嗎?寫給母親的詩有沒有唸給她聽?
莫 渝20
他們不懂,也不知道我寫詩。那時的作品,我曾裝訂成冊,留存下來,包括沒有發表的。我也寫過兩篇小說,沒有發表,保留在那本冊子裡。後來,就沒有再嘗試小說創作。
莊紫蓉21
為什麼沒有繼續寫小說?
莫 渝21
可能是懶惰吧?!
莊紫蓉22
如果你當時寫的小說能發表出來,可能情形就不同了。作品能夠發表也是很大的鼓勵。
莫 渝22
你說得對,作品能發表就是一種鼓勵。那時,寫的一些作品還是以母親為題材居多,跟母親感覺比較接近,似乎沒有想過要寫思念父親之類的文章。
莊紫蓉23
好可憐的爸爸!(笑)
再談談你曾經住過五年的台中吧。
莫 渝23
我剛進入師專不久,班上就舉辦到中興嶺的郊遊,坐車之後,還要走一段滿長的路,結果,我體力不支,竟暈倒了,剛好那裡是個軍營,有營裡的軍醫就近照顧。回來之後,我跟那位照顧我的軍醫,還維持長時間的通信連絡。我也覺得很奇怪,從小我就傾向於和年長者交往。小時候,有一年夏天,和祖父到崎頂(竹南北邊)祖父朋友的西瓜園,在那裡,我認識了一位到此休假的軍人(阿兵哥、充員兵),我也跟他交往,通信了一段時期。師專時認識的余成楠、陳恆嘉、陌上桑也都是年紀比我大。
我進師專第一年先認識余成楠,他在文藝社團講新詩的認識。第一年夏天的校刊,就登了我一首詩,第二年,他編校刊時,主要由我校對,臨時的補白也由我處理,那一期校刊登了我一篇散文、四首詩,其中一首詩是臨時補白的,匆忙間取餘光中詩集《藍色的羽毛》的「藍羽」為筆名(只用一次)。第二年夏天,我就開始有詩發表在校外的刊物了。後來認識了趙天儀他們,我就把《笠》詩刊引介到學校裡面來,放在學校福利社賣,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買。有一次,「笠」的年會活動(1965年冬)在後裡張彥勳家舉行,我曾帶了幾個同學一道參加。
莊紫蓉24
請你再談談台中時期的生活。台中沒有河流吧?
莫 渝24
台中沒有河流只有圳溝。
莊紫蓉25
那時東海大學工作營曾經幫忙清掃整治綠川那條圳溝。我也記得那條大水溝。
莫 渝25
到台中,一下火車站要到市區一定會經過「綠川」,沿著水溝兩邊有一些類似違章建築的房子,伸出到圳溝上,可能都是退伍軍人開的小吃店。再往西不遠有「柳川」,也是像「綠川」一樣的景觀,我記得有個估衣市場,那是賣二手舊衣服的地方。我剛到台中讀書時,「綠川」給我相當深刻的印象,因此,第一年,我就以「綠川」為筆名,寫了一篇短文登在校刊,那是我寫作的一個小小的起步。
莊紫蓉26
你怎麼會想到用「綠川」這個筆名?
莫 渝26
那時候,只是直覺地認為這個名字不錯,另一方面也覺得「綠」滿吸引人的,似乎暗喻著希望,後來,我也寫過一首詩,題目就是「綠」。這個筆名,我只用過一次。
綠川這條水溝現在已經加蓋成下水道,上面變成馬路了。最近,我看到台中的文史工作者印了一本綠川剪影的書,把綠川變成記憶中的一條河流。
綠川和當地的一些小吃店、小飲食店,也一直留存在我的記憶中。
莊紫蓉27
我記得我在東海大學讀書時,常常去那裡吃蒸餃。
莫 渝27
我也去吃過。我是個鄉下孩子,根本不知道什麼蒸餃。到了台中之後,發現很多新鮮的飲食品,有開了眼界的感覺。就這樣,「綠川」的印象一直留存著,感覺一個城市有這麼一條河流(水溝),能夠增添水文或是人文之間的互動。
莊紫蓉28
雖然只是一條小小的圳溝而已──
莫 渝28
對。也許那時水不太乾淨,但是,水是流動的,水的流動應該和車輛的流動有不一樣的感覺。
莊紫蓉29
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有很強的創作慾,你那時候寫了不少詩吧?
莫 渝29
讀台中師專時,因為沒有升學的壓力,所以閱讀了很多課外書籍,也嘗試寫作。在我往後所走的文學方向,有兩方面是對我影響滿大的。一個是覃子豪的《新詩講義》;另一個是覃子豪翻譯的《法蘭西詩選》。《新詩講義》對於我瞭解新詩和新詩寫作有啟蒙作用。這本講義分成兩部份,前面是「中國文藝函授學校。軍中文藝函授班」的講義,是屬於新詩的,第二部份是古典詩詞,我比較注意前一部份。《法蘭西詩選》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法國詩,到了七○年代,我學習法文以後,似乎,冥冥中引我從事法國詩的譯介工作。
莊紫蓉30
那時候你看了《法蘭西詩選》之後有什麼樣的感受?
莫 渝30
倒沒什麼強烈的感受,只是初步認識了一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譬如龍沙(洪薩)寫的<給海倫>這首詩,後來我才知道那是詩集《給海倫十四行詩》裡面其中一首詩。這首詩的主題是珍惜生命,結尾「生命的玫瑰今天就要去採擷」,有把握當下、珍惜現在的意涵。以後我也翻譯過這篇作品,標題是:<當你老的時候>,當你老的時候也許會回憶起年輕的時候的種種,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把握當下。
| 莫渝先生 於板橋寓所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31
類似這樣的想法有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譬如有格言式的,可是用詩寫出來,就給人不同的感受。
莫 渝31
對。詩讓你慢慢進入其中,而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法蘭西詩選》裡所介紹的都是一些法國有名作家的代表作,譬如拉馬丁的<湖>,維尼的<狼之死>。維尼是屬於堅忍型的詩人,<狼之死>這首詩裡面就富有堅忍的哲理,狼雖然被獵人打死,可是牠強忍住痛苦而不哀號。不論命運如何折磨,我們都要強忍住,不要隨便發出呻吟,露出可憐狀。
當時法國文學的書刊不太多,我只是從這本書得到一點初步的認識,以後有機會閱讀更多法國文學時,就有更深的感受。
莊紫蓉32
你寫詩背後的動力是什麼?
莫 渝32
除了有這樣的接觸和閱讀之外,一般來說,詩是較屬於青春的文學,自己感覺用詩的方式比較能夠表達,就依照閱讀的經驗與前人的寫作方式,試著把心裡的感受表達出來。我也寫散文,但是不多。
莊紫蓉33
不管用詩、散文或小說的方式,總是心裡有東西想要表達。你怎麼會有那些東西要表達?也就是說,是什麼觸動了你的寫作?
莫 渝33
有時候是感情方面的;有時候是受到了某一種刺激;別人的作品撞擊力也有,所以就慢慢地走上寫作這條路。在那個年代,多少會接觸倒一些比較晦澀的詩,特別是「創世紀」詩社的作者表現方式,讓我覺得詩可能不需要表現得那麼直接,可以晦澀一點。那是我師專三年級的時候,也就是我開始寫詩一、兩年後的情況。當時,也有大量的「藍星詩社」的詩集流落到書店,那是因為1963年10月,覃子豪過世後,原來放在他家裡的很多詩刊詩集流落出來,我購買了一些,無形中,在閱讀方面就增加了不少,當然,難免會感染到他們那種脫離現實的寫作方式。
莊紫蓉34
你在師專五年當中,詩的創作量不少吧?詩風有什麼樣的轉變?
莫 渝34
那時候,我寫詩是多方面的嘗試,一開始純粹是個人的表現,後來慢慢地隨著當時的詩壇而有較晦澀的詩出現,譬如<晨之死>(後來發表在《笠》第13期),這樣的作品都是當時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後來我的詩集就沒有將這樣的作品收進去。所以當時詩壇上流行的晦澀詩,還是影響到我。
| 莫渝先生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這種晦澀的歪風──現在來看是歪風,在當時儼然是詩壇的主流──,延續很久,所以我一直到退伍後進入社會做事,慢慢地感覺寫那樣的詩沒什麼意義,才有所改變。
另外,我想談談自己對文學整個概念有深刻認識的兩本書,對我啟示很大,一本是李辰冬的《文學與生活》(有兩冊),他還有一本《文學新論》,這兩本書最重要的是建構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從中我認識到整個中國文學的概念。另一本是東海大學高葆光教授寫的《詩經的新評價》,這是我師專四年級時自己閱讀的。過去很多文學的概念多半是文以載道那種泛道德主義,強調文學要有道德的訓誡,要依附在道德或政治裡面,詩經也一直是被這樣的看待,但是高葆光這本書是以純文學的角度來看詩經。他的說法肯定了我一向對文學的看法。不同於學校老師的說法,這本書提出文學的另一個角度與看法。
在人生觀方面,我在新竹讀書時曾經在圖書館借到一本書《生死與人生》,這本小書裡面提到蘇格拉底以及其他人的人生觀,蘇格拉底這一篇讓我印象特別深,最後談到人生的境界強烈的生命,讓我深深地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我們必需努力奮鬥。可以說這本書啟發了我對人生的看法。
莊紫蓉35
你在看這本書之前,對人生有什麼想法?
莫 渝35
那時我只是個初中的學生,可以說渾渾噩噩的。這本書讓我們從前人的經驗得到啟發,像蘇格拉底臨死前的坦然態度,對我有所啟蒙。
在台中師專最後一年,我看了梵谷傳,書名叫《生之慾 》(《Lust For Life》),或許譯成《熱愛生命》更恰當。
莊紫蓉36
就是後來餘光中翻譯的那本?
莫 渝36
對,是一個美國人寫的,我在師專的畢業旅行時買的,是正中書局的版本。這本書也給我不少啟示,以後我寫了一篇文章提到,我從梵谷學習到對藝術的追求,使生命能夠發揮出最高的價值。
還有一本唐君毅的《人生之體驗》這本書,讓我體會到自我的重要,肯定自己的作為。當時這本書是從圖書館借來的,裡面的一些文句我曾經抄在筆記本上。
這三本書讓我在人生的肯定的意義上,建立了初步的人生觀。
莊紫蓉37
這三本書似乎對人生都抱持著比較積極的態度。你有沒有看過比較消極的書?
莫 渝37
那時候看過哪些書也不太記得了。而這三本書是,我一看到就很喜歡。
莊紫蓉38
那是否跟你的性格有這樣的傾向有關? 有人天生就比較悲觀;有人則是樂觀的。
莫 渝38
後來我開始工作之後,有一段時期也遇到困境,難免會有消沈的時候。但是無形中總是有一股鞭策的力量。
莊紫蓉39
記得上次你曾經說過,小時候看到民族英雄之類的書,就會熱血沸騰也想有一番作為。是不是你內心裡頭就存在著一種積極奮進的精神,所以看到這一類的書就很容易起共鳴?
莫 渝39
我不知道。但是表哥給我一本《勵志文粹》的書,我就沒有從中得到什麼啟發,反而傳記給我的啟示較大。
莊紫蓉40
應該是這樣,說教式的文章,總是比較難以讓人接受。
莫 渝40
不過,有時看看自己的作品,偶而也難免有一種自怨自哀的味道。記得張愛玲曾經說過:「有一天我們的文明無論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有這惶惶的威脅。」像荒涼、悲涼、淒迷、寒愁等等悲劇性的語詞,在我的作品裡面還是會出現,這種悲慼的想法、感受,還是會存在我的詩裡面。兩者之間是否有衝突,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在行為方面,儘量不讓自己慵懶怠惰,但是在骨子裡的本質還是會透過詩表現出來。
| 莫渝先生與莊紫蓉 陳秀喜作品討論會 攝於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1997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41
人不會只有一面,往往有不同的兩面,甚至多面。或許因為你內心裡面是悲觀的,在行為上就更想要表現出積極樂觀來。
莫 渝41
我覺得詩文學有安慰的性質。詩所建構的是一個虛無縹緲的世界,經過長期的讀詩、寫詩,我的體驗是:不論是在療傷或愉悅,詩文學的閱讀與寫作,都在建構一個看得到或看不到的遠景,也許看得到;也許看不到,但是都是一種虛擬的方式。詩文學所建構的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因為不是真實的,所以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你會得到安慰,這是所謂的療傷;或是看了很高興,這是愉悅。或許我就是這樣,自己不愉快,可是要建構一個美好的文學世界;自己快樂,反而虛構出一個假象出來。
文學本身就是虛構的,雖然背景有某種真實的點存在,可是它表現出來的是虛無縹緲的。
莊紫蓉42
跟人生的很多狀況一樣,真真假假,有時候虛構的東西給人很強烈的真實的感覺;真實的事物卻反而讓人家覺得虛假。
莫 渝42
是啊!
莊紫蓉43
當兵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莫 渝43
當兵時,我到過澎湖、高雄林園左營、彰化北斗、恆春車城等地。
莊紫蓉44
這幾個地方當中,哪裡印象較深?你是什麼軍種?
莫 渝44
在澎湖當兵時印象較深刻。在澎湖我寫了一些作品,那時我開始用紀德的方式寫筆記,寫了一些隨筆。
我是海軍陸戰隊,屬於砲兵團,部隊移防時都有軍車。從澎湖調回台灣就在高雄林園一帶,冬天時到彰化北斗,過年時,在左營一個月,當時我不知道葉石濤住在左營,春天又到南部車城附近。部隊調動時除了坐船、搭火車之外,就是車輛行軍。後來我以這樣的經驗寫了一首詩<南方的陽光>,南部那種亮麗的陽光給我很強烈的感受。我會寫這麼一首詩,是看到法國詩人佩斯寫的<遠征>這首詩,他派駐中國擔任外交官時,到蒙古沙漠大戈壁探險旅遊時所寫的。我追記這一段軍旅生活的感受,主要是把它當作一種嚮往南方豔陽的經驗,背後動機跟佩斯的<遠征>有關。
在車城,我待了三個月,從四月到六月,我們駐紮的地方在海邊的防風林裡面,不遠處的沙灘,整天是亮麗的陽光,相當刺眼,十分迷惑人,那種感覺一直留存在我心裡。後來看了佩斯的詩,加上當兵的那一段經驗,引發了我類似遠征這樣的念頭。如果說法國詩對我的觸發,除了先前的閱讀之外,這段經驗應該是比較明顯的。
莊紫蓉45
<南方的陽光>這首詩,你所要表達的主題是什麼?
莫 渝45
主題是讚美陽光,生命的歷程當中對陽光的接納。佩斯有一個詩句用叉戟來形容陽光,真切地形容出陽光的刺眼和灼傷力,那種感覺,我在南部真正體會到。
莊紫蓉46
你當兵時還有什麼特別的經驗?
莫 渝46
我在左營時,遇到元宵節,街上有長列陣頭的遊行活動,當時我對這類民俗活動很排斥,總覺得這是一種迷信,甚至將之與義和團聯想在一起。後來年紀大一點之後,才比較能夠認同這類的活動。那時候年輕,對這類民俗滿排斥的,我寫過一首<沒有神的廟>,也是站在同樣的立場,表達對迷信或民俗的忽視。現在我的想法就不一樣了,覺得應該接納這些民俗,因為這是很鄉土的東西。所以目前我在蒐集整理台灣新詩中有關民俗表現的資料。
莊紫蓉47
這些民俗活動應該有很深的內涵,不只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樣而已。
莫 渝47
嗯!可能當時新文學對迷信有一點排斥,才會有那樣的想法。也許我沒有受到宗教教育,不知道宗教的價值跟內涵,跟宗教、廟會有關的都會排斥。年紀大了以後,慢慢地體會到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份,就能夠接納了。
莊紫蓉48
退伍之後,你被派到海邊的學校?
莫 渝48
先是到貢寮海邊的一個小學,學生少,有時會帶小孩子到海邊玩,真的是把戶外當作教室。
在詩的寫作方面,自己感覺處理得更精緻,意象也表現得更精確。有一個經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趴在桌上休息,突然抬起頭來看到對面亮麗的青山,直覺地就寫出這樣的詩句:「猛抬頭迎面青山逼我解繳雙目」。這樣的表現是說,太美麗、太亮麗、太青翠的東西,一下子可能沒辦法接受,有不希望再看到的感覺。到了八○年代,我翻譯《比利提斯之歌》的時候,第五篇寫一個住在山上失明的老人,年輕時,因為看到林澤女神而眼睛瞎了,幸福便成了他遙遠的回憶。也就是說他看了太美的東西之後,就失明了。
莊紫蓉49
是不是可以說,看過最美的東西之後,就不需要再看別的了,或是別的東西不再值得看了。另外,眼睛瞎了之後,這美麗的東西就永遠留存在心裡。
莫 渝49
嗯!所以他說「幸福便成了遙遠的回憶 」,他把這美的東西一直留存著。
莊紫蓉50
剛剛你說的看到青山的那種經驗,寫下來的詩也有這樣的意涵嗎?
莫 渝50
那時只是一種不敢再看那青山的直覺,也許那是一種視神經的反應也說不定。
莊紫蓉51
當時,你還沒有看過《比利提斯之歌》,就有這種類似的感覺,可見文學有共通性。
莫 渝51
所以有人說過,文學沒有獨創,可能你是在重複別人的痕跡,因為你所表現的,可能前人都表現過了。
莊紫蓉52
不過,也不會兩個人所表現的完全一樣。
莫 渝52
有文論家說,作家只是在踩著別人的腳印往前走。
莊紫蓉53
剛剛你說看到青山不敢逼視的感覺,讓我想到你<背影>這首詩最後一句,希望陽光刺瞎你的眼睛,不忍看到父親孤獨衰老的背影。這兩個對像不同,一個是亮麗的青山,一個是衰老的父親,不過同樣地都不希望再看到,前者是眼睛被繳械;後者是希望陽光刺盲自己的眼睛。一個是很美很亮麗的東西讓你受不了;一個是很孤單寂寞的親人讓你不忍心看。這可能是你比較消極的一面的表現吧?
莫 渝53
我也不知道,<背影>是一種親情的不忍割捨,覺得沒看到就不會有心痛的感覺。
莊紫蓉54
這是一種逃避,是比較消極的吧?
莫 渝54
消極,我不否認啦。
離開貢寮之後,我到林口國小,在那山上我寫了幾首詩,譬如<泥鰍之死>就是看到頑童抓到泥鰍又把牠弄死的情形寫的。那時,是我個人經濟各方面比較困頓的時期,周夢蝶的一些詩也給了我支撐的力量,他的詩句當中難免也有悲觀的表現:「這苦結/除卻虛空粉碎更無人解得!」(詩〈落櫻後,遊陽明山〉),這樣的觀點,好像說除了毀滅,一切才能消失。我覺得這樣的詩句,無形中也支撐著自己不要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莊紫蓉55
這等於是反面的作用。
莫 渝55
對。
林口是在山上,周夢蝶的<囚>有這樣的詩句:「青山外,一輪斜月孤明,誰是相似而猶未誕生的那再來的人呢?」這就是對未來的期望,雖然把自己囚住了,但還是希望往後有人來讀你的作品。如此的寄望,讓人覺得生命仍然有存在的意義,寄望於未來。
那時候,我開始參與「後浪詩社」的活動,在詩方面,有一群朋友在一起,多半是早期師專的前後期校友。
莊紫蓉56
在林口那個時期,你說生活上比較困阨,那麼所寫的詩會不會比較消極灰色;或是相反地寫些積極的詩來鼓勵自己?
莫 渝56
那時,我已經開始寫兩個系列的詩作,一個是「在我們的土地上」,這個系列主要是描述我們的環境,帶有批判的性質;另一個系列則是一般的感受的書寫,比如說<含羞草>、<自囚>這兩首,表現獨自忍受困阨的心態;另外,像<暖雨>、<月光曲>就比較積極,<水鏡>也是那時候寫的。有一首<風之姿>,所表現的應該可以算是以詩解詩,還有其他的含意,把所有的樹砍掉了,看不到風,結尾說「天天等候筆端的枝葉,擺出最佳的姿勢」這是對文學的一種期望。
到板橋是1975年之後了,後浪詩社《詩人季刊》慢慢分散,詩的活動減少了,我離開不久,鄭炯明介紹我進入「笠」;在這之前,我已經在《笠》發表過不少文章,特別是法國詩的介紹,所以趙天儀或是李魁賢說過,這個階段由於我介入法國詩的翻譯,使得《笠》的譯介方面更豐富,因為早期《笠》的外國詩譯介,偏重在日、美、英等國的詩,法國幾乎沒有。
莊紫蓉57
那時你還沒有去法國吧?
莫 渝57
還沒有,當時我在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法文系就讀。我會接觸法國文學,除了讀法文系的因素之外,早年看了覃子豪那本書也有關係,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冥冥中似乎有所安排。
莊紫蓉58
你進入「笠」、定居板橋、遊學法國之前這段時期,你寫的詩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莫 渝58
這個階段,我慢慢走向寫實。寫意方面,仍然繼續以前描寫內心的感受;寫實則落實在台灣本土。
莊紫蓉59
寫意的部份,在心情感受上跟過去有什麼不一樣?
莫 渝59
可能在用詞上有所不同,從排斥晦澀的詩之後,就避免太艱深、刻意的文詞,比較平實、甚至是平凡的文字來表現。
莊紫蓉60
在主題內容方面有什麼改變嗎?
莫 渝60
沒有太大的改變。這時期我自己認為稍微可以看的作品有,<苦竹>、<夜寒聽簷滴>,還有「父親靈前的焚稿」那幾首詩。
莊紫蓉61
像<苦竹>是寫意和寫實兼有的嗎?
莫 渝61
基本上,應該算是寫意的,如果說有寫實的話,大概就是童年對竹林的印象。
莊紫蓉62
你好像很喜歡<夜寒聽簷滴>這首詩,你是在怎麼樣的動機下寫的?要表達什麼樣的意境?
莫 渝62
這首詩的重點是,雖然天是黑暗的,但是天與地之間說不定存在著某種契合,人處在天地的中間,應該和天地也有達到契合的可能。人的憂愁雖然是屬於個人的,可是詩本身就是表現一種愁,「詩言志」,「志」,也可以說是一種心事、個人的愁,個人的愁能夠跟天地結合。冥冥中好像有一隻手輕輕地給予撫慰。
莊紫蓉63
所以,在整個宇宙當中,個人並不是孤獨的。
莫 渝63
像李白所謂的「與我同消萬古愁」,這是他個人的愁,但是這「愁」是存在於天地之間的。也許各人的愁不一樣,但是,這種個人的愁悶,古代有之、現代有之,往後也會有,它是瀰漫在天地之間的。
莊紫蓉64
是不是可以說,每一個人的愁,具體的是不一樣的,但是把這愁抽像化了之後,其實是相同的,可以引發共鳴。
<水鏡>是什麼時候寫的?
莫 渝64
<水鏡>1968年12月27日軍旅中,駐紮彰化北斗時的初稿,修改後收進詩集《無語的春天》(1979)。最近我整理舊稿,發現我原來寫的和定稿不一樣,改了很多。我到法國之後,回想自己寫過的作品,想到<水鏡>裡的一些詩句,像「淒美」這樣的語詞,我一直滿喜歡的。「擁抱一株淒美,投胎最最怡然的寄情」,這樣淒美又怡然是衝突的。花朵本來是一種怡然的東西,可是水仙的前身是一則淒美的故事,由淒美產生一種怡然。詩文學是不是有同樣的情況?當時我有這樣的想法,就對這首詩比較注意。
莊紫蓉65
你到法國也有跟水親近的經驗吧?
莫 渝65
到了法國,才曉得河川的可愛。我們的淡水河不見得會讓人家喜歡。我來到北部後,淡水河已經因為工業的發展而受到污染,小時候親水的經驗已經不見了。我在法國時是在羅亞河的支流緬因河邊,我住的城市剛好橫跨緬因河。法國在水利方面做得相當好,沿著河有一條快速公路,河堤整理得很乾淨,河岸可以停放小船,平常船主把馬達拿走,假日才帶來,將船開到河心釣魚。河面約二、三十公尺寬。河的西邊是個大湖泊──緬因湖,常有水鴨和帆船。從我的住處到緬因湖,小徑上相當多的樹木,大約四、五十分鐘的路程,。那是個十萬人口的小城市,有一個古堡,法國十六世紀詩人杜伯雷所住的一幢小屋子還保存著做為杜伯雷陳列館,城中也有一所杜柏雷中學。
由於河川整理得很好,令人很想去親近它,經常想到河邊流連徘徊,跟我們的淡水河不大一樣。因而引發我進一步思考河川和人類發展的過程。從法國回來之後,我寫了一篇<嗚咽的淡水河>,談到淡水河受到污染的情形,還寫了一篇<珍愛我們的生存空間>,提出一些跟環保、生態有關的看法,主要是河川的問題,希望能夠趕快讓河川重生。在國外,一個城市往往建築在河川的兩岸,把河川變成城市的一部份。我們則往往以河為界,分隔兩邊,這樣在管理或維護上都可能會互相推托,不會把河川當成一個共同體。
在法國,透過這樣的體認,覺得河川更值得我們珍惜,所以我寫了一組詩,就是以「羅亞河畔的思念」為主題。
莊紫蓉66
你很早就接觸法國文學,後來就讀淡江法文系,又到法國留學,親身到生產法國文學的地方。過去你是透過書本了解法國以及法國文學,後來親身到法國之後,有什麼樣的想法或感受?
莫 渝66
第一個是印證了過去書上所看到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白楊樹,以前讀到白楊樹(Peuplier),總無法領會那是什麼樣的樹,到法國親眼看了之後,才真正體會到。它的枝幹不會橫生,也不會往下伸,所有的枝幹都是往上長的,這樣一直往上的樹木,的確令人喜愛、敬佩。
其次,是日常生活的飲食,譬如喝咖啡,我們理所當然一定加糖、加奶精,他們則分得很清楚。理髮,我們是包括洗頭、剪髮,他們則理髮就只是理髮,不含洗頭,加上洗頭的話,價格不一樣。像這樣細節分得很清楚,就有清單的出現,不像我們比較含糊。所以有人說法文很明確,我想跟他們的生活有關係。
還有就是排隊的習慣,到郵局或去哪裡辦事情,大家都會排隊,不會有人插隊,顯得很有秩序。
此外,他們的廣場很多很特別,每個廣場都有個名字。更重要的是路名街名有很多人文氣息,哲學家、詩人、醫生,只要是有名的或是當地的,都可以用作街路的名稱。讓我們感覺文化相當深厚,而且深入到民間,已經變成生活的一部份。
莊紫蓉67
你在法國期間,體驗到不同的文化,有沒有特別讓你想寫的主題?
莫 渝67
當時我要寫的有兩個系列,一個是「羅亞河畔的思念」,一個是「浮雲集」,不過「浮雲集」寫得不順利,只有<小毛驢>和「清泉的聲音」。
莊紫蓉68
「浮雲集」的主題是什麼?
莫 渝68
李白的詩句:「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這種漂浮的感受帶來的鄉愁,<小毛驢>就是表達鄉愁。「清泉的聲音」主要是描寫法國當地的景觀,比方說白楊樹或穴居農莊。當地郊區有一處農莊,它比路面低,早期居民住在低於地面的房舍,目前已經闢成一間農具展示所,把古代的農業用具大大小小各種樣子都陳列出來,並推出紀念品與景觀明信片,還有一個地下走道作為聯絡各處的通道。這是由於地理因素形成的一個特殊的穴居式農莊。這兩個主題是詩的部份。另外,我還留下一些類似筆記之類的文章,後來我陸續整理出來,就是《猶裡西斯手記》,那是我的一些隨筆,以
及讀書心得。
| 莫渝先生著作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莊紫蓉69
你在法國大約一年,這段期間你在思想觀念或是心情、詩的創作上,有什麼改變?
莫 渝69
可以說對文學產生懷疑是在這個時候,感覺上,文學是縹緲虛無的。以前只是想到要寫,沒有做深入的思考。真正對文學的反思,是在這時候,覺得自己用心寫的,好像不夠踏實。文學是個死堆棧,虛無縹緲,很想放棄,可是放棄了文學,又能夠抓住什麼東西?所以還是又繼續從事文學的寫譯工作。就是這樣在猶豫搖擺不定之下,走走停停。我感覺自己的文學路程有這種狀況。
莊紫蓉70
你對文學的反思是思考到文學的功用嗎?
莫 渝70
對!會想到文學的功用或實用價值。對個人而言,好像不能夠從文學得到什麼好處,可是又為什麼持續在做?所以就有一點既猶豫又踟躕。對文學反思是我在法國時期的第一個思考點。
其次是對鄉土的更加認識。在法國,即使是個小鄉鎮,也有他們的文學作品,有的用他們的方言來表現,當地人都相當重視在地作家。1983年四月份有一個詩歌節,他們舉辦活動,朗讀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很多都不是法國文學史上有名的。外國人所認識的法國文學相當豐富,而他們國內每個小地方的文學也同樣很豐富,雖然那些不一定在文學史上留名,但是他們還是能夠自得其樂,把詩和生活密切地結合。
另外,早先在台灣時,法國詩刊或文學資料比較不足,到法國以後,資料的取得比較容易,我就希望能夠將法國20世紀詩選做得更完整更詳細些。
第三點是他們的遊行示威活動令我印象深刻。我去法國那一年,台灣還是戒嚴時期,雖然有了黨外雜誌,但是所有的示威遊行都是禁止的。我看法國的遊行示威很有秩序,那一次的示威是因為做屋頂板岩的礦場要關閉,國家要從外國進口板岩,原來的工人即將失業,他們就集合起來變成全國性的抗議,剛好遊行到我所住的城市。我看他們遊行時,小孩子也參加,後來我把這個事情寫成<稚子何辜>這篇文章。我深深體會到這只是弱者的一種抗議手段,也沒有引起衝突。看了這樣有規劃、有規矩的示威活動,我感覺任何一個遊行示威都是弱者的行為,如果沒有外力介入,只是表達他們的心聲,孩子也跟著遊行是很不得已的。我回台灣之後,黨外活動變成政黨活動,遊行抗爭相當激烈,幾乎每一次的遊行示威都會有衝突發生,表示我們太過於情緒化了,特別是政黨政治之後,這樣的情緒化更為嚴重。
莊紫蓉71
你文學的路走了幾十年了,你對文學的看法是什麼?你認為文學是所謂的無用之用嗎?請你就文學方面講幾句話。
莫 渝71
在愉悅與療傷的過程中,詩文學的閱讀、寫作,都在建構可視或不可視的遠景/美景(遠景不見得是美景)。有時對文學會有無奈的感覺。八○年代以來,台灣的社會形態一直在改變,文學逐漸被漠視,早期對文學的雄心多少受到影響,於是走在文學路上,就不免有走走停停的現象。不過,在走走停停當中,是越來越接近台灣文學,六○年代我所接觸的文學是中國意識下的文學,雖然自己閱讀或創作也有一些台灣的東西。到了七○年代,我介入法國詩的譯介,八○年代,雖然還繼續譯介法國詩,也做第三世界其他國家詩人作品的翻譯工作,到八○年代中期之後,幾乎都回到台灣文學的閱讀與進一步地認識,希望台灣文學不再被忽視。
九○年代以來,我一直參與苗栗縣的文學編撰工作,推動文學創作之外,我們希望建構「苗栗文學史」,凸顯地方文學的特色,讓長期從事文學創作的文字工作者,能夠受到家鄉的重視。不管是編「苗栗文學讀本」、「文學史」,策劃一些書刊,或「苗栗文學全集」的構思,都希望能夠從地方走向國家的文學,這是我的期望。
莊紫蓉
感謝莫渝先生接受訪問。
並收進《台灣新詩筆記》,莫渝著,桂冠圖書公司,2000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