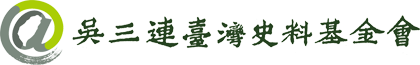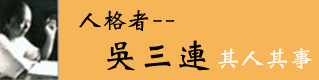探索語言的藝術,追求現代精神--陳千武專訪
 |
時 間:2001年10月12日 10:30am~15:00pm 地 點:台中市陳宅 |
莊紫蓉1
人活在世界上,受到時間、空間的影響很大。請您先談談小時候住的地方。您出生於南投的名間?
陳千武1
對,名間本來的地名是NAMA,是平埔洪雅族居住的地方,日本人來了以後就依照原來的音安上漢字「名間」,還保留原音NAMA。後來「名間」用台語、北京語讀,就失去原來的音了。中國來了之後,很多地方的本名都用漢字加以改變,這是很不應該的。日本人則不同,很重視原音,都是保持原來的音,不會隨便改用漢字。從語言上來講,應該保留原來的音才對。
莊紫蓉2
名間的自然環境是怎樣的?
陳千武2
名間是在山腳下。台中盆地從後裡沿著大安溪和大甲溪一直到濁水溪,一邊是中央山脈,一邊是八卦山脈通到彰化,再過去是大肚山,通到大甲,中間被大肚溪斬斷,一邊是八卦山,一邊是大肚山。但是山脈造成了寬廣的台中盆地,這是台灣很特殊的一個地理。這一帶溪流很多,濁水溪、大肚溪、烏溪、大甲溪、大安溪,所以古早的人要走路到台中很困難,台中的開發較晚,就是因為交通困難。我出生的地方就在濁水溪旁、八卦山脈頭的山腳下一個叫做弓鞋的地方。
| 陳千武 2001年10月12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3
那裡的風景一定很好囉?
陳千武3
嗯!風景很好,一邊可以看到中央山脈,另一邊可以看到彰化平原,一直過去看到海。
莊紫蓉4
您從小在那裡住了很多年?
陳千武4
我在那裡住到讀台中一中三年級時,因為讀書的關係,家就搬到豐原。我在台中一中讀書時不是好孩子,是「歹囝仔」,我父親認為這樣不行,孩子的教育比較重要,就辭掉名間的農業技士職務,在我堂伯陳水潭(豐原名醫,後來做過豐原鎮長、台中縣長)幫忙下,轉到豐原。之後我在豐原住了三、四十年。
莊紫蓉5
剛剛您說您在台中一中讀書時是「歹囝仔」,是怎麼「歹」?是愛看閒書、文學書吧?
陳千武5
呃!文學的書是台中一中一年級時開始看的。我小學讀了三年的公學校,那是台灣孩子讀的學校,之後我進入日本孩子讀的南投小學校,所以我公學校讀了三年,小學校讀了四年(我三年級讀兩次),這四年當中都和日本孩子在一起,講日本話,很瞭解日本人的生活,常常去日本同學家,他們的父母都很親切,拿餅乾給我吃。經過那樣的生活,我的想法就不一樣了。
小學六年級畢業後,我考進台中一中,第一天校長上修身課時,我就被他叫起來罰站,他說我跟旁邊的人講話沒有聽他講課。他問我剛剛他講什麼,我把他剛才講的話重複講一遍。他是日據時代很有名的校長,有四十幾年的教學經驗,他帝國主義的思想很重。
| 台北市客家藝文中心 《台灣處分–一九四五》新書發表會 鈴木茂夫(圖左)、陳千武(圖右) 2003年4月26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6
是廣松良臣嗎?
陳千武6
對啦!我站起來把他講的話講出來,那些話是很有道理的,他說,會在廁所亂畫亂寫的,關門留下縫隙關不緊的人,是不會成功的。他說我沒聽他講話,結果我能夠把他講的話說出來,表示我有聽他講話啊。這樣一來他反而生氣了,我就被他罰站。開學第一天就被罰站。哈哈哈!
莊紫蓉7
那時您被罰站心裡會不會覺得不滿?
陳千武7
不會啦!我知道校長為什麼生氣,我瞭解他的心理。我就被罰站直到那節課結束,我們那一班的同學都認識我了。
莊紫蓉8
小學時您為什麼從公學校轉到小學校?
陳千武8
我讀的皮仔寮公學校,在名間山上,我每天上學要走五、六公里的路。讀到三年級時,日本話會講了。我父親是日據時代農林學校畢業,在農業試驗廠當農業技師,他知道去小學校讀書,一切都不一樣,可以瞭解日本的種種,所以他希望我能夠進小學校讀書。當時是有錢有地位的台灣孩子才能讀小學校,南投小學校三十多個學生當中,連我算在內只有三個台灣孩子。我父親帶我去小學校,由校長親自考我日語,再調查一下我的家庭狀況,就讓我轉入就讀了。
莊紫蓉9
您覺得公學校和小學校有什麼不一樣?
陳千武9
差很多啊。公學校雖然有台灣老師也有日本老師,但是公學校是對殖民地小孩的教育,小學校是他們日本小孩的教育,比較正常。因為公學校是對殖民地小孩的教育,所以強調要會講國語。其實,在日本也沒有「國語」這種說法,只說是「標準語」。台灣因為是殖民地,就強調日本國的國語。小孩子剛入學當然不會講日語,學到稍微會講日語就禁止講台語,否則會受處罰。這是不一樣的地方。另外,老師教學方法不同,教科書也不同。所以,我到小學校之後才感覺很自然,感受到正常的教育。而透過天真的孩子之間的交往,可以瞭解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和日本人的想法。
莊紫蓉10
在小學校讀書時,你有沒有感覺受到日本人的歧視?
陳千武10
日本人很「心適」(有趣),你的實力如果比他差,他就會歧視你,但是如果你的實力比他強,他反而尊敬你。日本人的性格和台灣人不一樣。我在公學校一年級時,站在我前面的一個女生東西掉了,我幫她撿起來,拍一下她的肩膀,這樣就不行了。放學回家時,她和她父母在廟旁等我,她父親一看到我,一句話都沒說就打我巴掌,和我一起放學回家的堂哥問他為什麼,她就說我欺負她。我堂哥問我什麼事,我告訴他,是她的東西掉了,我幫她撿起來,她瞪我一眼。我堂哥跟她說,你應該感謝他才對啊!她父親聽了才沒有話講。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男女受授不親的時代。在小學
校就不一樣了,下課時間同學不分男女都在操場玩,常常玩摔角,有個女生力氣很大,男生都摔不倒她,大家看到我在旁邊看,叫我去摔她,結果我一下子就把她摔倒了。像這樣,公學校和小學校
| 陳千武作品 《陳千武集》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就不一樣了。那時我力氣很大,沒有人打贏我,因此就贏得他們的尊敬,讀書我也不輸他們啊!所以日本人不會欺負我,反而班長常常邀我去他家玩。他父親是學校的公醫,有一次我要站起來時手往後一按,被一把豎在那裡的刀子割了一道傷口,他馬上帶我去讓他父親治療。我覺得日本孩子很守規矩,講道理,有禮貌,家庭教養很好。那班長會教我到他家要如何對待他的父母。日本人是這樣的,很有教養,尤其到台灣來的日本人。
但是,日本人有很強的優越感,尤其對那些他看不起的人,他的優越感就表現出來。如果你有實力,比他強的,他就降伏你、尊敬你。
莊紫蓉11
這可以說是日本精神的一種嗎?
陳千武11
不是日本精神,是教育的問題,他們的家庭教育、風俗習慣的緣故,我們台灣人如果也是這樣教育,也是會這樣。
| 台北市客家藝文中心 《台灣處分–一九四五》新書發表會 鈴木茂夫夫婦、陳千武夫婦(由左至右) 2003年4月26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12
您讀小學校,和日本人相處很好,可是在台中一中時卻能起來反對改姓名運動。
陳千武12
我讀公學校,再讀小學校時,就思考﹕一個台灣為什麼有公學校和小學校之分?一邊是台灣孩子,另一邊是日本孩子?為什麼日本人比較優勢?那時我就感受到了。有一次放學我從小學校校門走出來準備去搭車回到十三、四公里遠的家,隔壁不遠的公學校有幾個孩子把我圍起來要打我,我心裡並不怕,準備和他們打。後來他們之中一個說﹕「這不是昨天那個日本囝仔啊。」,他們就走了。原來他們是要打日本孩子。遇到這種事情,我就會想﹕同樣在這個地方,怎麼會有台灣孩子和日本孩子的差別?越想就越清楚地知道,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政府來管台灣。稍稍從歷史來看,也可以瞭解台灣的地位,台灣的命運。
我反對改姓名運動是中學五年級第一學期的事。
台中一中三年級我留級一年。三年級第三學期,我沒有註冊,拿著註冊費72元打算到日本去打天下。我怕家人擔心,在台中火車站搭車時寫了一封明信片告訴家人我要搭船去日本打天下。明信片一送達家裡,我父親馬上到學校找校長告知這件事。校長立刻打電報到船上,船長派事務長來找我去見他,他問我要去日本做什麼,我說要去日本打天下,做苦工也沒關係,但是我還要再讀書,做一個像樣的人。為什麼我想去日本?因為當時日本和台灣的狀況不同,台灣是殖民地,日本則沒有殖民地的差別,所以張文環、楊逵他們都到日本接受國內的教育。我認為要讀書或是寫作,日本的環境較好。當時很多台灣人都有這種想法。船長聽了,講了一句話讓我很有感受,他說﹕「去日本也不一定會比較好,什麼事情都要會臨機應變,不要固執一定要怎麼樣。」船到了蒙市,事務長帶我到船公司買了一張票讓我搭另一艘船,交代那位船長保護我回來台灣。
莊紫蓉13
這也是一段很特別的經歷。您那麼小就會想到日本、台灣的差別,會有自己的想法。
陳千武13
在那樣的環境,和台灣孩子、和日本孩子在一起,就會去思考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其實,日本孩子對我很好,因為做事情我不輸給他們,對他們也很好,不會有什麼差別。
莊紫蓉14
您待人很好,好像從小就這樣了?
陳千武14
台中一中時,我是問題學生,哈哈哈,老師都怕我。
莊紫蓉15
問題學生也有很多種。
陳千武15
當然很多種。哈哈!當時有幾個日本老師會特別照顧我,例如英文老師,體育老師。我還擔任樂隊指揮,美術設計方面我的表現也不錯,我又會賽跑,是柔道初段。不過,我的成績不是很好,因為我不愛讀書,都在看文學書。
莊紫蓉16
您的興趣很廣啊。
陳千武16
嗯!那時我是兩百公尺和四百公尺的賽跑選手。有時候晚上台中一中(台灣人子弟為主)和台中二中(日本人子弟較多)的學生爭吵打架,他們就會來找我,那些台中二中的日本學生看到我就跑了。哈哈哈!
日本孩子很阿莎力,不會記恨。公學校時,同學彼此吵架,一個月都不講話,最快也要兩三個禮拜才會和好。小學校就不一樣,早上在運動場打架,日本孩子被我打得流鼻血,中午就和我握手言和了。性格不同。
莊紫蓉17
民族性不一樣嗎?
陳千武17
嗯!民族性不一樣。現在和日本人交往,也是和台灣人的交往不同。台灣人普遍很會忌妒,日本人也會忌妒,也會與你對敵,但是台灣人比較「暗肚」。這可能是民族性。
莊紫蓉18
您讀小學校,常常和日本孩子在一起,會學到他們那種阿莎力、不記恨的性格嗎?
陳千武18
大概不是學他們,可能自己本身的性格傾向。如果不是我這種性格的人,譬如其他兩三個台灣人和日本人相處就和我不同。那些日本人看到我也不會有什麼台灣人日本人的差別,台中一中時,我和台灣人、日本人交往,都一樣沒有分別。
莊紫蓉19
您剛剛說台中一中時,幾位老師對您不錯—
陳千武19
對,英文、體操、農業(當時有農業種作的時間)、音樂老師都對我很好,其實校長也對我很好,哈哈,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問題學生,哈哈哈!
| 陳千武作品 《詩的啟示》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莊紫蓉20
「問題」,是喜歡打抱不平吧?!
陳千武20
這一點也有,譬如改姓名的事,本來應該聽學校的,但是我有意見啊。
莊紫蓉21
有意見又有行動。
陳千武21
是啊!對我好的老師都清楚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他們知道那理由並不是壞的。不過,也有不大好的老師,有一個國語老師,一個矮矮的日本人,三年級時,第一學期的作文,四百字的稿紙,大家通常都寫一張或兩張,那時我一天到晚都在看小說,我就用小說體寫了二十張交出去。一個禮拜之後,同學的作文都發回來了,我的沒有還我,我就問老師為什麼沒還我,他說他還在看。就這樣永久沒有還我,那學期我的作文成績是丙等。這老師也「九怪」。到了第二學期,每次他的課,我就把小說放在桌上,看我自己的書,他講什麼我都不聽。這樣一直到學期中,有一天上課時,他從教室後面繞到我旁邊站住,我不理他繼續看我的書。他在那裡站了大約兩三分鐘,然後回到前面講台,叫我的名字說﹕「出來!」,我離開座位走到前面去,我看他握緊拳頭發抖。當我走到他前面,他出手要打我時,我抓住他一隻手,用柔道把他摔在地上,他叫道﹕「你敢!你敢!」,同學看到這種情形都站起來了。我再把他拉起來讓他站著,他也不敢說什麼,桌上的書收一收就回去辦公室了。
莊紫蓉22
後來學校沒有處罰你?
陳千武22
我以為他會去跟校長說,所以我有受處罰的準備。但是,他不敢,他「見笑」啊!那學期我的成績是乙等。我很認真寫了二十幾張稿紙,他給我丙等,我都不聽課,還把他摔一下,卻給我乙等的。哈哈!也有這種老師。他後來不敢對我怎樣。
莊紫蓉23
您記得那篇二十幾張稿紙的作文寫什麼內容嗎?
陳千武23
忘記了,那麼久了。他如果還我,可能—
莊紫蓉24
是您第一篇小說。
陳千武24
是啊!哈哈!
※ ※ ※
莊紫蓉25
您在台中一中時,喜愛吉川英治的小說,他的小說有什麼特色?
陳千武25
他寫的是大眾小說當中的時代小說,也就是歷史性的小說,他寫得很好,很多人喜歡看。我看他的小說,覺得很有趣,就入迷了,於是,越看越多越廣,所能找到的日本的小說、世界名著,我都看了,我差不多都浸在圖書館裡面看書。台中圖書館的書看膩了,就跑到中央書局去找新的文學書。就在中央書局認識了經理張星建。他和張深切他們一起組織台灣文藝聯盟,有一段時間主編《台灣文藝》。我沒錢買書,都是站著看「免費」的書。那時候我家已經搬到豐原了,下課後必須到車站搭車回家,因為班次不多,常常要花一個鐘頭等車,我就利用等車的時間跑到中央書局看書,
今天沒看完的,明天繼續看,就這樣天天去中央書局看書。有一天,張星建(當時我只知道他是中央書局的經理,並不知道他是文學前輩)走過來,我以為他要來干涉,就把書放回書架。他看到我在閱讀文學的書,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你以後要看書就來這裡坐著看。」他拿他主編的《台灣文藝》給我看,我才知道台灣也有作家,也有文學。那時我是三年級。
| 陳千武作品 《台灣新詩論集》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後來我留級一年,再讀一次三年級,到四年級第一學期暑假,我就開始寫詩了,八月投稿《台灣新民報》,主編黃得時採用了我的詩,之後我就一直寫詩。那一年年底,在台中召開文學家會議,那時候台灣人作家大部分都在台中,台灣文藝聯盟也在台中,所以,我說台中是台灣文學的基本地,台北是統治者文學的基本地,戰後也一樣,現在還是這樣啊。
莊紫蓉26
您中學時看了很多日本文學、世界文學,後來才看台灣文學,您覺得台灣文學的特色或是水準如何?
陳千武26
台灣文學本身是我們自己的,有親切感,這是和日本文學、世界文學不一樣的地方。對我們有親切感的東西,比較會有熱愛的心情。
我投稿之後,有一次黃得時要到台中開會,他從台北打電話來學校找我。那時學校規定學生不能投稿,所以我寫的詩是用筆名「陳千武」發表的。
莊紫蓉27
您怎麼想到用「陳千武」這個筆名?
陳千武27
「千」是數目字,筆畫少,很容易寫,發音也不錯,有簡潔的感覺,「武」是我的名字中間的一個字,所以我就用這個筆名。
我是從吉川英治的大眾小說開始看,後來又進入純文學的小說。日本的大眾文學和純文學分得很清楚,純文學比較注重心理描寫等精神性的東西,大眾小說則偏向故事性,比較沒有追求精神性的東西。我看純文學的作品,更加入迷,因為可以看到心理描寫,人的美妙的心理動態都可以看到。純文學看很多之後,我開始讀詩。詩和小說不同,是用很尖銳的語言來表現。我是從短歌、俳句開始讀的,也有一段時間寫短歌。我不喜歡寫俳句,因為一首短短的十七個字,季節的東西要寫進去,規定很嚴格。我寫過短歌,一首三十一個字,比較長。但是,短歌的心理描寫、詩的表現種種,都不太合我的意思。因為人的複雜心情,用三十一個字很難描寫,所以我就往新詩方面。日本的詩分得很清楚,從新詩、自由詩、近代詩,到大正、昭和時期的現代詩,我都看了,越看越有興趣,就開始寫。
| 陳千武作品 《寫詩有什麼用》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剛剛我講黃得時打電話到學校,學校聽到台灣新聞報的編輯打電話找我,馬上就找我去聽電話。他說第二天要來台中,叫我到中央旅社見他。第二天我去到中央旅社,看到三個人在那裡﹕黃得時、張文環、葉寶越。那時我是個孩子,只是聽他們講話。張文環體格壯碩,講話豪爽,聽他講話很「爽快」。
莊紫蓉28
您認識了黃得時、張文環、張星建之後,有跟他們繼續來往嗎?
陳千武28
我當志願兵時,在台北訓練所,放假時就去山水亭找張文環。我當兵回來之後,他在銀行當經理,知道我在林場,來豐原時就打電話叫我出來一起吃飯。我到台中市政府當庶務股長時,他已經到日月潭大飯店工作了。有三、四次日本人來台灣找台灣文學作家,我都帶他們去日月潭找張文環。每次見到張文環,他都跟我說﹕「你那庶務股長不要做了,來這裡當經理吧。」不久,他就過世了。至於黃得時,就沒有機會再和他來往,說不定他也忘記當年叫我到中央旅社找他的事了。
我認識了張星建之後,每次去中央書局,先和他打個招呼,然後看我的書。四年級時,我知道楊逵也在台中,有時候放學後背著書包就跑去找他。那時楊逵是晴天種花,雨天讀書。知道我對文學有興趣,他太太葉陶對我很親切。
莊紫蓉29
那時您和張文環、楊逵都是談文學嗎?
陳千武29
大部分都是聽他們講台灣文學的種種狀況。而張文環、張星建、張深切、楊逵他們對我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情,經常對我說﹕「你對文學有興趣,會寫作,你要認真寫作,為台灣的文學,必須創作很多台灣的東西,將台灣的文學資產留給後代子孫,你要履行這樣的使命感。」他們每個人對我講的都是這樣的話。所以說,那時候的台灣文學家,每一個都很認真地想要寫台灣的文學,因為過去台灣的新文學沒有很多,文學作品不多,所以他們都拚命地寫,將台灣文學的資產留下來。所以,新文學從1920年開始,到戰敗的二、三十年當中,台灣的作品已經不少了,他們留下了不少的文學資產。三、四年前我翻譯張文環的作品就有好幾百萬字,光是一篇<山茶花>就將近一百萬字。
莊紫蓉30
您覺得他的作品怎麼樣?
陳千武30
台灣的小說家裡面,張文環的作品應該是最高的,他對台灣人的心理、人和人之間接觸的情形,都很用心描寫。就以去參加東亞文學會議的他和西川滿、龍瑛宗三個人來講,西川滿的小說有他的特色,他寫台灣的民俗、風俗之類歷史性的,張文環寫的是深入台灣本土的東西。這方面龍瑛宗較差,他是站在日本文學的立場在寫,我翻譯他的作品時,發現他很喜歡用外來語,表現出他接受了很多世界潮流的文學。張文環就沒有這種東西,他都是很認真地描寫梅山鄉下人的生活。講起來,張文環的本土性很豐富,可惜戰後他的全集到現在還沒有出來,能夠看到他的作品的人較少。
莊紫蓉31
他的全集快出來了吧?
陳千武31
說是11月會出來,也不知道到時候能不能出來,已經兩三年了。
張深切和我母舅是很好的朋友,我一、二年級時住在我母舅家,當時他在北京教書,如果回來草屯,常常會去我母舅家,看到我,就摸摸我的頭說﹕「認真讀書哦!聽說你喜愛文學,以後創作多一點。」他也是這麼講。所以,這些台灣前輩作家,每一個人都有建立台灣豐富的文學資產的想法,認為有這樣的義務,有這樣的使命感。
莊紫蓉32
他們自己努力創作,也鼓勵後輩創作。您也沒有辜負他們的鼓勵。
陳千武32
哈哈!這是一種興趣啦。
莊紫蓉33
剛剛您談到張文環對台灣本土的描寫比龍瑛宗更深刻。就文字的表現來看,他們兩位又是如何?
陳千武33
文字表現上,龍瑛宗的日文比較好,剛剛我講他比較有日本文學的氣味,就是文學語言的用法比較好,比較有日本正統語言的味道。張文環則帶有台灣日語的味道,他的日語也不錯,也有相當的水準,只是和龍瑛宗相比,龍瑛宗的日語較好。但是張文環寫出來的作品比較有力量,感動的力量較強,龍瑛宗的作品比較美,但是比較沒有力量。
戰後國民黨政府來了之後,要將日本文化消滅,規定不能講日語,不能看日本電影,也不能聽日本音樂,把當時台灣有日本色彩的東西通通拿掉,種下中國的東西。在詩的發展上,這一點比較少人考慮到。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那些外省詩人,說台灣沒有文化,沒有文學,紀弦就這樣講。那是因為日據時代台灣作家拚命創作要留下來的文學資產,都被國民黨消滅掉了,都被封鎖起來了。例如台中圖書館,有日文的東西,第一代的莊遂性館長就把日文的圖書都放在地下室保管。第二代那個外省人館長把那些書都拿去燒掉了。所以,國民黨政府來了之後,台灣的文化資產、實際上的資產,損失了多少啊!現在才說要做捷運什麼,台灣那麼多鐵路,都被廢掉了,那是很可惜的。例如從這裡要到田尾,或是到彰化,糖廠的鐵路都有啊,台中到南投也都坐糖廠的火車,為什麼不把這些鐵路留下來?所以,台灣的資產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多少啊!不但這樣,那些看不見的文化資產,都被消滅掉了。現在才要從新翻譯出來,像張文環的,到現在還拿不出來。所以我覺得很悲哀。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外省詩人來台灣建立了三個詩社﹕現代詩、藍星、創世紀,開始要在台灣播下中國文化的種籽。紀弦現代詩在台灣要開始推行現代文學、現代精神,所謂「橫的移植」。中國五千年的文化資產怎麼可以被取代?不行啊!新詩的現代思想不行。餘光中很聰明,馬上改變他的現代主義,變成新古典主義,他開始推動新古典主義,那是傳統的,就沒問題了。創世紀更聰明,他提倡超現實主義。照理說,超現實主義比現代主義更加前進、更前衛,為什麼紀弦的現代主義不能推動,而超現實主義到現在還在推動?《聯合報》、《中國時報》都依照這超現實主義的方針在推動的。但是他那超現實主義和真正的超現實主義不一樣,那是「超脫現實」,和現實沒有關係,不會觸及政治,不要緊,所以一直到現在還有。他們的文學獎的得獎作品,沒人看得懂。以前創世紀他們就開始寫他們那種超現實主義的詩了,有一次一個詩人寫了內容是歐洲的文化、戰爭的詩,我將它翻譯編入《華麗島詩集》在日本出版,那時候台灣的詩人和外省詩人還在一起,所以《華麗島詩集》裡面有好幾位外省詩人,三大詩社的作品都在裡面。我譯好了之後就問他,為什麼不寫台灣自己的卻要寫歐洲的,他說﹕「歐洲比較好寫啊。」。他不敢寫台灣,因為那會冒犯到政策。
| 陳千武作品 《詩文學散論》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台灣現代主義的現代詩不可以,超現實主義的詩可以繼續到現在,就是因為它是超脫現實,和現實無關的,讓人家看不懂,就不會影響到民眾的思想。現代詩的現代精神,就是民主、自由、獨立,閱讀現代詩就會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所以國民政府就壓制現代主義。
到現在,笠詩刊是寫台灣本土的,比較寫實。但是笠詩刊在寫實當中有用到現代主義,例如我寫詩有很多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新即物主義。我提倡新即物主義來對抗他們的超現實主義。新即物主義在德國也是抵抗超現實主義而產生的。所以,當時我就開始寫新即物主義的詩、提倡新即物主義,這是很現代精神的東西。但是他們的報導比較強,聲音比較大,《聯合報》、《中國時報》都在提倡他們那種詩。我曾經參加過《中國時報》的評審,都是那一類的詩,我看不下去啊,這種詩只是將文字湊起來,有一點趣味,是一種文字遊戲而已,沒有思想,也不會產生思想。我的詩
,每一首詩都有思想。
莊紫蓉34
講到思想,您在台中一中時聽到校長講了那一句話之後,您就開始思考人、人生的問題。您對人生的思考,階段性的成長過程是怎樣的?
陳千武34
我接觸文學之後,會想﹕文學有什麼用?在這個社會,文學好像沒什麼用處。但是,透過文學才能認清自己,我在靜宜大學教書也跟學生這麼講。像連戰講的,他說﹕「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這是什麼話?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台灣人就是台灣人,怎麼會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模糊嘛。所有的一切都把它變成模糊,這就是大陸的矇膿詩。台灣也一樣,因為獨裁專制的國家,不喜歡讓人民有真正的現代主義的思想、現代精神。日據時代也是這樣,壓制現代精神,這就是愚民教育啊。超現實主義的方向就是離開政治的政策,所以不會有問題。這就是思想的問題。
日據時代,水蔭萍吸收了1928年在日本產生的詩和詩論那種現代主義思想,拿到台灣來,1935年成立風車詩社,推動超現實主義。他推動的超現實主義是真正的超現實主義,不是像創世紀那種超脫現實。但是出了四期之後就遭受攻擊而停刊。那是日本時代帝國主義不允許推動現代精神的思潮,以避免產生自由民主獨立的精神。這種現代主義的思潮,比林獻堂他們文化協會推動的文化啟蒙運動更厲害,如果水蔭萍的現代主義一直推動下去,影響會更大更深入,所以就不被允許。
| 陳千武作品 《台灣民間故事》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二十多年的時間,西川滿可以說是代表性的作家,他是法國文學的專家,應該接觸過法國的超現實主義,但是他在台灣為什麼不推動現代主義?他在台灣都是寫那些浪漫的東西,小說都是現實的,他並沒有touch到現代主義的思想。1928台灣詩人協會出版《華麗島詩刊》,推動現代新詩精神。如果這本詩刊繼續下去,台灣的現代思潮就起來了,但是只出了一期就停刊,詩人協會也解散。為什麼?主要的原因是它推動現代主義精神,統治者不喜歡。戰後的狀況也一樣。
莊紫蓉35
這樣講起來,文學的作用很大。
陳千武35
是啊!作用很大啊!一個人接受多一點文學的東西,思想就不一樣,會認清個人存在的價值,就會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剛才我說過,我讀小學校時,在那樣的環境,我就感覺到我一個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社會裡面應該怎麼做。
台灣文學,日據時代是以小說為主,現在也一樣。其實,詩才是比較尖銳的東西。現在很多人談台灣文學,台灣文學的精神是什麼?台灣文學的風格是什麼?不是現代主義,是寫實主義。日據時代是寫實主義,現在還是寫實主義,不敢脫離寫實主義進入現代主義,為什麼?台灣人很乖,台灣作家也很乖啊,政府不讓接觸現代主義的東西,自己也不想去接觸。我們說要重視台灣文化,台灣的官員、立法委員都沒什麼文學教養,如果有文學教養的話,我們的政治會更好。
為什麼台灣的文學一直到現在仍然停留在寫實主義,而無法進入現代主義?這就是問題了。所以台灣的殖民統治,從日據時代到現在,思想都被控制了,自己無法突破。現在也一樣,大家講台灣文學都不談詩,只講小說。
莊紫蓉36
您寫詩也寫小說。中學的時候,您的興趣就從小說轉到詩。不過,1990年代您還有寫小說—
陳千武36
我是從小說開始進入文學世界的,本來也有意思要寫小說。但是,後來讀了小說再讀詩之後,感受到詩的精神活動的重要性,就此脫離不開了,所以我的寫作一直以詩為主。對我來講,詩是主要,小說是副的;對整個台灣文學來講,小說是主要,詩是副的。不講主副,台灣文學如果對詩更看重,更用力推動的話,台灣文學將會更完整、更好。
日據時代以小說的寫實主義為主,詩不受重視。但是當時很多寫小說的臺灣作家也寫詩,龍瑛宗也寫詩,只有張文環沒有寫詩。然而他們的詩沒有前衛性,沒有現代主義的精神。戰後大家說要重視臺灣文學,但是沒有重視重要的精神性的、心靈的活動。
我寫小說不是要寫有趣的故事,我是要寫一個人的心理動態。所以我的小說讀起來不是很有趣,我注重的是語言和心理描寫。
莊紫蓉37
心靈的探討—
陳千武37
對!那比較重要。
莊紫蓉38
您剛剛說閱讀文學可以瞭解自己,就這一點您可以舉例說明嗎?
陳千武38
我剛剛談到我在台中一中時,為什麼會反對改姓名運動,這都是因為從文學而認清了自己﹕我自己有我的自我,我為何要改姓名?這樣的思想會產生出來。所以,如果在臺灣推動現代詩、現代精神,將會影響很多人,讓他們瞭解自己,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可以判斷事情的好壞,對善惡可以分得很清楚,這是文學的功能。多接觸文學,這樣的思想就自然會產生出來。這樣的人多的話,統治者就很難統治了。所以臺灣的殖民政策和日本本土不一樣,日本沒有被人家統治,雖然是帝國主義,但是他們可以接受世界性的現代主義,他們的文學比臺灣自由。臺灣作家應該要有這樣的認識,例如寫臺灣本土的小說,要考慮到小說裡面的思想,能夠影響到讀者的思想嗎。張文環、張星建、楊逵他們當年對我講的﹕「為了臺灣,你要努力寫作。」到底要努力什麼?不是作品寫很多就好,是要透過作品影響民眾的思想。讓每個人認清自己做為一個臺灣人應該怎樣。作品要能引導民眾的思想,臺灣文學才有價值。
莊紫蓉39
您有特殊的讀書經驗、四年志願兵的南洋經歷,戰後在林場工作,您的人生很豐富。您在深山裡面工作時,和原住民接觸的情形,可以談談嗎?
| 陳千武作品 《活著回來》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陳千武39
那是工作上的,我在八仙山林場是擔任人事的工作,管理工人,照顧工人。我不是用做官的心態對待他們,而是照顧他們的生活和工作,讓他們的工作做好一點。我是用那樣的心情對待他們。我本身當兵,被管的時候,不是用直接的方式抵抗,要先瞭解日本軍隊的體制,做一個日本兵,和同年兵被管的心情都一樣。為什麼會被管?透過文學可以對臺灣殖民地的體制清楚地瞭解。文學是一種反抗,但是也要瞭解了才會知道要如何抵抗,我並不是直接抵抗。當然有時候要直接抵抗,像改姓名運動,我叫全校學生不可以改姓名,否則就抓來打。其實那只是手段而已,主要是要讓大家瞭解改姓名會讓我們變質。問題就在精神,精神和精神的接觸,人類愛等等,都會產生。所以用那種立場對待人,讓人家瞭解。有文學的教養,才能發覺事、物、現象的本質。很多人對本質沒有深入思考,這就是沒有新詩的現代精神。現代性的東西很重要,李登輝能夠推動民主,就是有現代精神,才會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所以,教育很重要,中國在臺灣五十多年來沒有「人的教育」,就是沒有現代精神的教育,用皇帝制的封建思想來教育,人民會現代化嗎?會真正瞭解自由、民主嗎?李登輝八十歲了還要出來,就是這樣,這一點我們要瞭解。
| 陳千武作品 《獵女犯》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莊紫蓉40
您的現代精神是從文學來的?!
陳千武40
當然從文學來的。
莊紫蓉41
不過,您好像也有接觸哲學,譬如海德格,是透過日文接觸的?
陳千武41
是透過日文。很多也是由文學而瞭解的,例如伊裡亞德的詩,或是存在主義,都是透過小說、文學認識的。有一段時期日本共產主義文學流行的時候,我也浸淫過,當時共產主義的文學,我差不多都看過。
莊紫蓉42
剛才聽您談到小時候和日本人相處的經驗,提到你強的話,他會佩服你。您的小說《獵女犯》裡面好像也有這種精神。您在南洋當日本兵的經驗也是很可貴—
陳千武42
對啊!那是在生死之間。
莊紫蓉43
戰爭結束您還在南洋時,曾經辦一個「明台會」,那是什麼性質的組織?
陳千武43
那時還不能回來,從爪哇到新加坡的都在一個集中營裡面,每天就是等船,無事可做,我就和林益謙商量組織一個明台會,希望以後回臺灣之後能夠繼續連絡,可以做一點事情。於是,明台會就成立了。開始的時候,用明台會的名義組織一個戲團演戲,以臺灣為題材演出舞台戲,劇本由會員撰寫,過去演過戲的就當演員。明台會裡面什麼人才都有。我又提議發行一個報紙型的刊物,大家交換精神性的東西。於是就到新加坡集中營管理營軍的地方借鋼版來,請人寫好文章,拿來自己刻、自己印,發給集中營(將近一千人)裡面一個隊幾份,一個禮拜印一張,四、五個禮拜才印四、五張而已。當時有很多人寫。
| 第六屆國家文藝獎頒獎 台北紅樓 2002年9月20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44
為什麼取名「明台」?
陳千武44
「明理臺灣」的意思。
莊紫蓉45
您兒子的名字和這有關嗎?
陳千武45
後來我就把我的大兒子取名為「明台」。之後,很多人用這個名字,明台中學、明台公司—-
莊紫蓉46
戰後228事件,您有什麼經驗?
陳千武46
當時我在八仙山林場上班,我想去參加,但是必須上班,又結婚沒多久,我那些戰友不讓我參加。
莊紫蓉47
有感受到那種氣氛吧?
陳千武47
有一次在街上,一大群人追一個外省人,那個外省人被追到了,跪在地上求大家不要打他。我剛好經過,發現那個外省人是林場裡面的人,就替他說情。大家就放過他。228 時,我就遇到這件事而已。之後是思想問題,白色恐怖。我二弟被抓去關了兩三年,他是台中商業學校畢業的學生,該校有老師被抓,從老師那裡他們發現了學生的名單,我弟弟因此被抓,其實他沒怎樣。說起來真是亂來,就這樣白白被關了兩年。
莊紫蓉48
戰爭剛結束時,好像不少人對祖國(中國)有所憧憬,但是228之後—
陳千武48
我在爪哇就碰到了。戰爭結束,因為船期的關係,我們在那裡等了一年才回來。在等待期間,我們想,已經回到祖國懷抱了,就去找中國大使館,說我們是臺灣人,想要拜託安排船期返台。不料卻被趕出來,他說﹕「你們和日本軍來的,應該去找日本人啊。」中國人就是這樣。那時就感受到了。
莊紫蓉49
1951年您在《軍民導報》發表了一篇日文小說,那時不是禁止日文了嗎?
陳千武49
那時候政府禁止日文,只有《臺灣新生報》有一個<軍民導報>副刊,日本的岡崎郁子也來查過《軍民導報》。因為禁止日文、日語,但是原住民不會講台語、客語,漢字也看不懂,所以政府為了讓原住民瞭解政令或消息,才設一個《軍民導報》,算是軍部辦的,是用日文發行的,將近一年就停了。那時日據時代寫過東西,日文不錯的張建在《軍民導報》主編副刊一樣的東西,小小的篇幅。當時苗栗的羅浪,錦連都寫過,我只在那裡發表過日文小說<哀愁夜>這一篇而已。詩的部份,我曾經寄了一首給張建,在他的散文集裡面提到這首詩。
莊紫蓉50
您從日文轉換到中文,很苦吧?
陳千武50
轉換的痛苦是有。我們講的臺灣話,文法和中文一樣,但是日文的文法就不一樣,有時候顛倒。所以將台語思考的轉變成中文,是很困難,也不是很難。不過,文章要看得多,才能習慣它的用法。
莊紫蓉51
您抄《少年維特的煩惱》中譯本來學中文?
陳千武51
對。那本書日據時代看過日文本,有一次在書店看到中譯本,就買回來看看中文是怎樣寫的,一邊抄一邊學習。抄過印象比較深刻,有人不喜歡翻譯別人的作品,怕受到原作品的影響。我不一樣,我很喜歡翻譯別人的作品,翻譯是一種再創作,翻譯當中,我可以瞭解原作者的心理,對原文和譯文這兩種語文做比較,語言的音韻變化。譬如華語或是台語的一句話,譯成日文時,有好幾句日文意思相近,要採用哪一句日文才能符合原文的情、景。有些句子的意思一樣,但是意境、意象是不同的,尤其是詩,更有這種狀況。所以,我很喜歡翻譯,就是可以訓練自己的寫作。
莊紫蓉52
您講過文學語言、日常語言、真實的語言,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陳千武52
語言都是一樣的,文學的語言也是使用我們平常在講的語言。語言是文學的一種工具,但是我們在應用的時候,如何把日常使用的語言變成文學的語言,這要看創作開始的時候的動機,開始創作的動機是文學性的,所採用的語言就會變成文學性的,如果創作時的動機是散文的,所用的語言就是散文的。散文的語言就是日常所用的語言。
| 第六屆國家文藝獎 陳水扁(左)、陳千武(右) 2002年9月20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詩的語言一定要提升到詩的境界。詩的語言不是早就存在那裡的。過去臺灣很多外省詩人說,詩有詩的語言,要找到詩的語言來寫才可以。那種詩的語言是別人做的,不是自己創作的。寫詩必須自己創作,要創作自己詩的語言。那麼,如何創作詩的語言呢?就是我剛才說的,寫詩的動機本身就是詩,找出來的配合它的語言就是詩的語言。我告訴我的學生說﹕「你們每個人心裡面都有一首詩,你自己沒有發現而已。以後你仔細注意你心內的詩是什麼,發現之後就用語言把它寫出來,你的詩一定很美。」那內心裡面的東西本身就已經有詩的東西了,用語言寫出來,就是詩的語言。如果心裡面的東西是散文,沒有詩的東西,寫出來的就是散文,就是日常用語而已,不會變成詩的東西。詩和散文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裡。
寫詩當然要經過訓練,但是,很簡單,我說你心裡面有一首詩,不管是喜怒哀樂,蘊藏在你內心的,很高興的,就用高興的語言寫出來;很痛苦的就用痛苦的語言寫出來,那就是詩了。
莊紫蓉53
您講過,詩是一種本能。問題是,大部分的人都無法發現這個本能。
陳千武53
是啊!那是因為他沒有去思考。每個人都有愛情,但是到底這是真愛還是假愛,很多人都沒有深入思考、分析。一個寫詩的人,或是喜愛文學的人,都會思考愛到底是什麼,這是詩的東西。很生氣,也是詩的東西。小孩子會講話就會寫詩了,因為他會講話就想要發表他心裡面所有的東西,詩就是心靈的活動,心裡想什麼就寫什麼,就是詩了,不必用很美的語言,美的語言是造的,不是真的詩。
我舉一個例子,鄭順娘文教基金會的鄭順娘是霧峰林家的媳婦,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921 大地震,霧峰林家的房子倒了,她很鬱卒。我有時候去她那裡和她談談詩,之後她就開始用詩寫出她的心情。她把她寫的拿給我看,問我說那是不是詩。我說那正是詩,心裡所想的寫出來,就是詩了。今年初她印了一本詩集《窗外的花朵》。她寫了詩之後,那種受到地震的鬱悶心情才平靜下來。
莊紫蓉54
這是文學的一個作用。
陳千武54
是啊!所以,如果心裡很痛苦,就去寫詩。如果夫妻吵架,心裡很難過,靜靜地去寫詩,把吵架的原因、情況種種好好考慮,寫下來,一切都解決了。
莊紫蓉55
不過,要寫詩還牽涉到表達的問題。
陳千武55
我說,會講話就會寫詩了,把最真實的心情,所感受到的寫出來就對了,不必什麼技巧。小學生寫詩很簡單,例如「媽媽的愛」看不到,但是他會寫啊﹕「媽媽的愛是一盆滿滿的洗澡水/我躺在裡面睡著了」。可以躺在裡面睡著,那種安心、溫暖,就表現出來了。寫詩的人都會考慮語言的意義性,所謂語言的意義性是,這個語言從哪裡來,如何發展,這句話可以讓人家感受得多廣、多深。
莊紫蓉56
這樣說起來,是不是對語言瞭解得越深入,越能夠真切地表現心情?
陳千武56
沒錯,但是,對語言的瞭解,是由思考而來的,所以詩就是思考的語言的藝術。語言的藝術化,才是藝術的東西。音樂也是藝術,但是音樂的音藝術,聽了就知道,不必怎樣思考,聽melody就感覺快樂了。詩不一樣,它必須要深入思考,瞭解其語言的意義性,去感受。詩也是一種藝術,但是比起其他的藝術,它是最基本最尖銳的。我們政府五十幾年來都不重視詩,說不定政府知道詩的厲害,故意加以忽略。
日本的詩人都瞭解文學的重要,家庭婦女也寫詩,我們臺灣人則沒有這樣。大學裡面文學科系的女生比男生多,她們在大學裡面讀了四年文學,畢業之後,文學哪裡去了?都不見了。為什麼會這樣?這是文學教育的問題。我剛剛講的,封建式的教育和現代思想的教育不同,現代思想才能符合現代社會的生活,古典文學讀太多沒用,那都是過去的東西,尤其封建性的東西,和現代社會不能配合。臺灣到現在還在用封建性的文學控制人民,這是一種殖民的愚民政策。
不瞭解文學的人,思考的範圍就很狹窄。所以,五十幾年的愚民政策很厲害到現在臺灣人覺醒的人還很少。藝術方面最尖銳的是文學,日本時代對文學就是這樣安排,不讓臺灣人有現代思想,戰後也一樣,一直到現在。有幾個作家想要突破呢?
莊紫蓉57
請您談談怎樣跟夫人認識、結婚的,好嗎?
陳千武57
我太太的父親是埔裡人,她媽媽是士林的凱達格蘭族。平埔族是母係家族。我太太的外公和杜國清的祖父是同一個人,杜有昭。他是個漢醫,背個藥箱從大陸來到臺灣,可能在淡水上岸,走到士林,被我太太的祖母招贅。不久,離開妻子,藥箱背著又跑了,後來流浪到鹿港開藥館成了一個有名的漢醫,他的書法也很好,前幾年杜國清曾經到鹿港帶了不少他祖父的書法去美國。有趣的是,他在鹿港賺了錢之後,又娶了幾個太太,但是每年都用轎子把大太太從士林接到鹿港住,每次總要住一個月以上,然後再把她送回去。
這也是一段很有趣的歷史,可以寫成一部有趣的小說,但是到現在我都還沒有時間寫。
莊紫蓉58
您是怎麼認識夫人的?
陳千武58
戰爭結束後一年,我從南洋回到臺灣,我家人都認定我已經不在了。那天晚上十一、二點,我和一個家在大雅的戰友在豐原下車,他已經沒有車子可以回大雅了,我要他在我家住一天,第二天再回大雅。我下車後就想﹕我家還在那裡嗎?我去南洋的四、五年間,是不是搬家了呢?因為我父親在鎮公所上班,於是我就去鎮公所打聽。鎮公所值夜的職員看到我,嚇了一跳﹕「你不是——你不是——」講不出話來。之前豐原街的殉難日本兵街葬(告別式),有我的相片,當時大家以為我已經死了。那個職員把鎮公所的門關好帶我回家。我家已經搬到距離鎮公所約五分鐘腳程的地方。我妹妹打開門,看到我也嚇了一跳。
第二天早上,就看到她(陳夫人)。她住在我家對面。就這樣認識了。
| 陳千武與夫人 台中陳宅大門前 2001年10月12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59
一看到就很喜歡?
陳千武59
當然是喜歡才會娶她。在爪哇集中營時,大家都會開玩笑,談到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結婚﹕「回去後第一個看到的那個小姐,就跟她結婚。」哈哈哈!大家都這麼講。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她,哈哈哈!就照這樣實施。
在戰地的情形和一般社會的情形是不太一樣的。我剛剛說去中國大使館被趕出來,心裡非常不甘心。說是「回歸祖國」,我來找祖國的大使館,卻得到這樣的待遇,這算什麼祖國的大使館?當時我們「明台會」約一千人,對此都非常憤慨,大家都很失望。難怪巫永福也很失望,但是他寫了一首叫做<祖國>的詩,那是還不知道祖國是怎樣的時候寫的。
莊紫蓉60
那時候大家對祖國不瞭解。
陳千武60
對!當時就覺得,這個中國沒救了。那種心情很難過。
我回來之後半年沒有工作,好在八仙山林場新上任的場長和我父親在農林試驗場讀書時是同學,我父親帶我去見他,他叫我第二天我去林場。第二天我去找人事課長,那人事課長是臺灣人,懂中文。他帶我去會計室考試,取來紙筆考我中文,叫我默寫國父遺囑。幸好我在雅加達時學過一個多月的中國語(當地叫做普通語)。當時同鄉會會長林益謙請了一個廈門人來教臺灣人普通話。我就在那裡學國語。我都沒學到什麼,就只會默寫國父遺囑。為什麼我會去背國父遺囑?因為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對臺灣的教育,學生要背教育敕語,當兵時要背軍人敕語。戰後學普通話時,我就想﹕在中國來講,國父遺囑應該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先把它背起來。
所以,在林場考試要我寫國父遺囑,我十分鐘就寫好了,他嚇了一跳,叫我第二天開始上班。哈哈哈!
莊紫蓉61
您還沒有講怎麼跟夫人認識、交往—
陳千武61
她是我堂妹的同學。我堂妹家住在南投,來豐原家政學校讀書。我太太當時住在她舅舅家,也就讀豐原家政。她們兩人都是從外地來豐原讀書的,感情特別好。我堂妹聽說我回來了,就跑來看我,我太太就跟她一起來,就這樣認識了。
我回來的第二天早上我出門回來時,看到她和我堂妹在我家幫忙我媽媽殺雞。我很訝異﹕「怎麼有一個美麗的小姐。」我猜想她是我堂妹的同學。那天晚上我堂妹帶她來我家,我們才開始談話。因為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就把日據時代寫的詩拿出來給她看。她就住在我家對面,我出門常常會碰到。兩三個月之後,彼此更熟識了。
她是在東京出生的,一直住在日本,戰爭結束前才回來臺灣。她家在台北,因為沒有學校可以讀,第二學期才到豐原住她舅舅家(就是杜國清家),進入豐原家政女學校就讀。她是第一名畢業的,到台中師範講習三個禮拜,然後被派到瑞穗國小教書,教了三十年才退休。
| 陳千武與夫人 2001年10月12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62
這是緣份啊,她從台北來豐原讀書,才會跟您認識。
陳千武62
她沒有來豐原的話,我也不會跟她認識,也不會回來第一個就看到她。不過,她母親很反對她嫁給我,因為我一隻手受傷。那是戰後在同鄉會時發生的事。集中營鐵路的一邊是英軍,另一邊是印尼,當時發生印尼獨立戰爭,聯合軍派日本軍隊去對付印尼獨立軍,我是機關鎗手,必須出去跟印尼軍打。但是印尼軍的將官都認識我,因為我在同鄉會的宿舍在荷蘭這邊,同鄉會本部在印尼那一邊,我每次回本部都必須經過鐵路邊的印尼獨立軍駐在所的關卡,守關卡的將官出來問我時,我就向他們說明﹕「我是從臺灣來的,臺灣是你們的哥哥。因為你們印尼被日本統治了五年,臺灣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所以,就被日本統治而言,我們是你們的哥哥。」他們聽了都說﹕「啊!對哦!」印尼當地的人就是這麼單純。我要過那關卡時,說一句﹕「蘇卡諾,萬歲!」,他們也說﹕「蘇卡諾,萬歲!」就讓我過關了。我的機關鎗要開打時,先喊一聲﹕「要打了。」,然後「答答答」打在樹木。他們也「答答答」打在樹上。我和印尼獨立軍建立了這麼好的友情,臺灣人同鄉會裡面卻有一個姓葉的利用臺灣人可以過關卡的方便,載整卡車的物品做走私的生意,賣給荷蘭人民。後來被印尼警察署發現,向同鄉會警告。同鄉會開會討論如何處理這件事,我提出建議要他以後不要再走私。開完會,當我要出去時,他躲在門後,用刀子猛向我的心臟刺過來,卻刺到我腋下。送到醫院急救,醫生發現神經都斷了,印尼醫院的華人醫生不會接神經,傷口一直不癒合,一個月之間,神經抽痛得不能入睡,晚上跑到外面凍露水,才稍稍減輕痛楚。後來轉到日本軍的醫院把神經接起來,痛楚才消失。但是因為時間太久了,沒辦法完全接好,所以,我的手指無法伸直。
在返回臺灣的船上,同鄉告訴我那個刺殺我的人也在船上,他們說要把他丟進海裡,我阻止他們。算我「歹運」,我也沒死,就放過他吧。
| 陳千武(左)、與莊紫蓉(右) 2001年10月12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