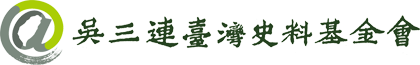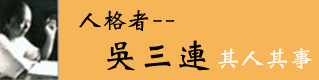田埂上的詩人──吳晟專訪
 |
時 間:2000年7月11日 地 點:彰化縣溪州吳晟宅 |
莊紫蓉1
您小時候在溪州生活,有很多特別的經驗吧?
吳 晟1
每個人的成長一定和他的童年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說到童年,其實也是有很多方面。第一方面,溪州是很偏僻的農村,我在這裡出生、長大,這一部份和一般的農村子弟沒什麼不同。我出生於半世紀以前的四○年代,那時候的生活,大家都差不多一樣──物質缺乏、要做很多事。我家是農村家庭,童年的生活和當時所有的農村子弟都一樣,有共同的經驗。這方面我沒什麼特別。
但是比較特別的就是我要講的第二方面。當時一般農村的人身體都不太好,而我母親身體卻很強壯,因此可以做很多的勞動。我父親是「吃頭路的」,日治時代當過警察、老師,戰後到公所、農會上班,總之都是吃頭路的。以前,吃頭路的是一種保障,一種穩定,一定比一般農村家庭在生活上更無慮。而且我父親很重視教育,因為他受過日本教育,知道教育水準對個人或是對整個民族都是很重要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樣,我吃得比較好,因為我母親強壯又很會經營。譬如一般來講,人家都吃蕃薯籤配菜脯,我們則一定有白飯,每天都有魚、肉、蛋。我能體會一般同學生活上的困苦,我常常會拿白飯去和人家換蕃薯籤飯吃。每天黃昏,端著飯和鄰居的孩子聚在一起吃,我就用自己的白飯換人家的蕃薯籤飯。我的理由是──我愛吃蕃薯籤。這是事實嗎?不錯,我也愛吃蕃薯籤,不過,其實我心裡想的是──他們都沒有白飯可以吃啊。在學校,我每天的便當裡面都有荷包蛋,大部分的同學都沒有,有些較貧窮的同學,一個大大的便當裡面只有蕃薯籤和空心菜。那時的我只是小孩子也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只是出於自然的同情,就會跟他說「你有空心菜?給我一點,我喜歡吃。那,我的荷包蛋給你。」。我常常會做這種事。其中有一個同學,跟我交換了幾次之後,一到午飯時間就找不到他。我想,可能其他的同學會笑他,而他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過去我們台灣人很「古意」,再怎麼窮也不會想佔人家的便宜。很「認份」,我有蕃薯籤就吃蕃薯籤,有空心菜就吃空心菜,不會想別人的好東西。這是台灣人的品質,窮得有尊嚴,不會忌妒別人。
| 吳晟先生 於彰化溪州的田園 2000/7/11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2
您有一首詩<野草>裡面有「我們是驕傲的」、「我們是卑微的」這樣的詩句,是不是表現台灣人窮得有尊嚴的精神?
吳 晟2
嗯!雖然他很謙卑,不過在謙卑之中有自尊。從小我就體會到我們台灣人有這種精神。譬如我家是開放式的,庭院寬廣乾淨,隨時都有一大群孩子在玩。我母親種的水果都是任意讓鄰居的孩子採摘,她如果到街上,常常會買一些炸果之類的吃食回去分給大家吃。而那些孩子,一方面愛吃,一方面很客氣。就是這種精神。
在物質生活上,我比起當時其他的孩子要好多了。做事方面,當然也要做,但是不像別人做得那麼多,有的同學根本沒辦法讀書。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每年都拿第一名,演講、作文、畫圖等等,除了體育之外,每一項都是第一名。那時我參加演講比賽,得過全縣第一名。我當老師之後,演講比賽也得過全國第三名。雖然小學時我各方面的成績都很好,但是我父親常常提醒我,並不是我真的比人家好,是我的機會較好而已。因為父親經常的提醒,使我不至於過於驕狂。
莊紫蓉3
我覺得您小時候的經驗對您的成長很重要。您各方面的表現那麼好,可能讓您很有信心。
吳 晟3
講到信心,這也是很難講的。其實,我是沒有信心的。我的經驗算是很特別,很多地方很有傳奇性。從小我就經常挨打,而且往往是很嚴重的責打。為什麼這樣?很重要的一點是,那個大環境、那個時代的教育方式就是打,父母打、老師也打,所以幾乎每個小孩子都免不了挨打,這是很普遍的現象。不過,我尤其被打得厲害,原因之一是,我父親受過日本教育,有那種「玉不琢不成器」的觀念,身為當地仕紳,孩子又都很會讀書 ──我哥哥、姊姊都是縣長獎 ──,所以每個新學期換了一位新老師,他就到學校拜訪老師,請老師特別嚴加管教。原因之二是,我比較「九怪」。現在我回想起來,所謂的「九怪」,是我喜歡當老大,好打抱不平。譬如看不慣大欺小而出手,或是當班長而有強勢作風,甚至常常和老師吵架。有時候我認為老師不對,就會抗議。例如三年級時,老師處罰男生沒有罰女生,當場我就說 「老師愛女生,老師偏心。」,以前的老師哪能容許學生這樣?一頓打當然免不了。四年級時的老師對我很好,訓練我演講比賽。不過她剛從師範學校畢業,才18歲,算起來還是個孩子,好勝心強,班上的成績都是全校第一。有一次被誤會我們班上的成績都是作弊來的,她就把我們幾個成績較好的趕出去不讓我們上課,要我們去把那個說我們作弊的人找來。那人不肯來,我就去向校長投訴。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不勝枚舉。
還有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相信很少人有這樣的經驗。我五年級時碰到彰化縣縣長選舉,國民黨的陳錫卿和黨外的石錫勳兩人競選。學校老師教我們唱一首歌「地方自治,初初實施──」
莊紫蓉4
是蔡培火作詞的那首歌嗎?
吳 晟4
是,但是詞改為「──,縣長由咱來選舉。──陳錫卿,百項能!」。老師教我們唱,要我們放學時沿路唱回家。我心裡感覺這樣很不公平,我就改唱「陳錫卿,腹肚硬硬」。至於石錫勳,我記得他的宣傳車播送的都很激昂。我就向一些較有錢的同學,一個人募來一角錢去買鞭炮,等石錫勳的宣傳車來了,我們一群同學就衝出去放鞭炮,宣傳車上的人就喊「囝仔兄,真多謝!回去要跟你們家的大人講。」。這樣平衡一下,我就覺得很高興。
在學校,有時中午老師要出去吃飯應酬,就交代身為班長的我要管好秩序,說他會慢一點回來。等到老師臉紅紅的回來後,發現全班亂糟糟的,就發脾氣說我為什麼沒管好。我回答說「你都管不好了。」。老師一聽,一巴掌就打下來,兩邊的臉頰紅腫得像紅龜粿。
回到家裡,父親發現我在學校被老師打,又打一次。以前我父母打孩子的方式很多種,用籐條、打巴掌都是很普遍的。我挨過的比較特別的方式是「升國旗」──用背孩子的被巾把手綁住吊起來打。還有一種是綁在柱子打,我母親經常這樣打我,我兒子也被我母親這樣打過。我母親身子肥胖跑不動,都是先把孩子叫過來,冷不防一把抓住綁在柱子上,一邊罵一邊打,然後她繼續去做事。等一下又回來打。被綁在柱子上,最苦的是全身被蚊子叮咬。
我經常挨打,除了因為自己比較「九怪」以外,有時候也因為欺負人家。所以,這種種情形之下,雖然小學時我都保持第一名,都當班長、大隊長。但是由於父母的要求和觀念、老師的教育方式,我挨打的次數特別多,最少有一百次──還不包括小打。不過,小時候我雖然挨了這麼多的打,但是我從來不會懷恨。老師們都和我很好,而我父親和我最要好,常常騎鐵馬載我,兩人一路談話聊天。該打的時候還是打,打完了仍然親密地聊天。
莊紫蓉5
您有感受到責打背後的愛,所以您不會懷恨。可能是這樣吧?
吳 晟5
嗯!我知道他們不是討厭我。尤其我父母親,非常嚴格的人格要求。
莊紫蓉6
您剛才談到您小時候經常是因為「九怪」而挨打。譬如說您跟老師頂嘴,您應該知道後果,可是還是會這樣做 ──
吳 晟6
那都是雄雄舉起來(一下子發作出來)的,沒有想那麼多。後來我參與民主運動、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其實就是從小這種打抱不平的個性使然。一個人的個性怎麼形成的我不知道,但是可以影響到他以後。譬如我小時候會替石錫勳放鞭炮,就是覺得不公平,為什麼我們替一個唱歌而不理另一個?當時我是不知道什麼黨,只知道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所以會靠往弱勢的這一邊。後來我替黨外的助講,幫忙寫文宣,所有彰化縣民進黨的選舉,大部分我都會幫忙。這種心情就是一種社會正義,是我從小個性的發展。
講回到我小時候經常挨打的影響,分成二部份。第一部份是,我本來的個性受到了壓抑。譬如說我從小就很大方,但是被打得變成很彆扭。《無悔》裡面有一篇<病情>寫我在80年代時,有一段時間,每次要演講就腳底發冷,面色發白,流冷汗,有時講到一半就倒了。其實我從小就很會演講的,但是那時卻發生這樣的狀況。要演講的前一天,我就睡不著。當然生理問題也有,我本來就有這樣的毛病,好好的忽然發作,天旋地轉,要躺好幾天,什麼時候要發作也不曉得。不過,演講時經常發生這種狀況,不只是生理的因素,也是個性上的壓抑造成的。我原來的個性就像我在<無悔>裡寫的,高中時看到警察打一個小孩,我不自量力地上前去打抱不平,結果挨了警察一頓打。事後我馬上去找張健,他是個讀書人,也不知道怎麼辦,而且那個時代也沒辦法怎麼樣。這是我的本性。這樣的本性被壓住,但是三不五時又會發出來。個性上的壓抑,讓我有時候很彆扭,有時候老大──照顧人、疼惜人──的性格又會跑出來。
| 吳晟先生與莊紫蓉 於彰化溪州吳晟的田園 2000/7/11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第二部份是,我變成很愛看書。到底我天生愛看書,或是經常被打才變成愛看書,我也不知道。壓抑的結果,原本很大方愛講話的個性,變成很孤獨,某些時候默默地不講話。那時我看了不少書,像森林打獵記、森林之王等等大自然、原野之類的書,我特別感興趣。我初中時最愛看的電影有兩種,一種是美國西部片,有一大片原野。對大自然的喜愛,跟我後來就讀畜牧也有關係。另一種是除暴安良、有俠義精神的電影,這可能是我個性的投射。
總之,我童年時代的大環境較為貧窮匱乏,不過,我家的經濟狀況較好,使得我有較好的機會,因而在學校的成績很好。但是又因為我的個性強而經常挨打,本來的個性受到壓抑,轉而養成愛看書的習慣。
莊紫蓉7
您父親是受日本教育的,他對您管教嚴格,不知道和所謂的日本精神有關係嗎?
吳 晟7
我是不很清楚什麼是日本精神。我父親接受日本教育,之後又在公家機關工作,當然一定會受到日本教育或日本文化思維的影響。以做人來講,那個時代的序大人都是中規中矩,是非分得很清楚,當然有一些是非不一定是對的,但是不管如何,他們分得很清楚。所以他就根據他的認知去做。
莊紫蓉8
您從小就愛打抱不平﹐那是否也就是作家的個性?
吳 晟8
不一定,因為作家有很多種,不一定作家在個性上都有某些傾向。
莊紫蓉9
基本上,作家會站在正義的一邊,為弱勢抱不平,或是較有批判性格。是不是這樣?
吳 晟9
這也要看個性,不必然每個作家都這樣,我們看到的就有很多不同的典型。講白一點,每個時代依附權勢的也很多,畏畏縮縮的也有,有的較明顯,有的較不明顯。譬如以我來講,說是天生愛打抱不平,喜歡替人家出頭。但是,我也有沒表現出來的部份,也就是說還是有隱藏,沒有完全表現。相對的,有些作家可能社會正義的部份較少,私利私心的部份較多。投機、私心的性格,每個人都有,並不是一個社會正義的作家,他的性格裡面就通通是社會正義。因為人是很複雜的,我們只能說他社會正義的部份較強;或是私心的部份較強。譬如說,我社會正義、社會關懷方面很強,我的文學裡面,社會議題佔大部分。而我個人的心情、戀愛情事,很少去寫。我寫我的母親、妻子、孩子,其實都和整個社會相關連。社會關懷是我的大部分,不過,我也有私心、懦弱,那是我的小部份。而有些作家是私心的部份更強。我們社會,尤其大約十年前,畏縮,為自己考量的部份較強的作家很多,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說他都沒有社會關懷沒有社會正義,只不過是他這一部份退縮了。有人縮得多,有人縮得少;有人表現得多,有人表現得少,不能決然地說某人是社會正義,某人是依附權勢。我認為今天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不能這樣地來劃分。因為每個人都有很多面,我們自己也一樣,畏縮、懦弱、投機、虛榮的一面,一定都有,差別只是在於這些部份所佔的比例是否掩蓋過社會正義;或是社會正義掩蓋過這些部份。是比例上的問題。
莊紫蓉10
吳濁流說過「拍馬屁的文學不是文學。」。您如何解讀這句話?
吳 晟10
我認為拍馬屁應該解讀作「不真誠的」。拍馬屁是拍誰的馬屁?我認為是善良的,我去歌頌它,這也是拍馬屁。拍馬屁的意思是讚美、講好話。如果說是諂媚,也是要看是向誰諂媚。所以我們的思考應該活潑一點,不要只限定在一個方向的思考。譬如我們不要把前輩作家神化了,並不是每個前輩作家都很完美,一定也有畏縮、怯懦、投機、虛榮等等性格。吳濁流本身有他了不起的建樹和貢獻,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在他的文學過程當中,也必須靠一些隱藏、迴避等等才得以生存。這些尚有爭議,我們不談。我要強調的是,每個作家都有各種個性上的比例。
至於吳濁流說拍馬屁的不是文學,因為這種講法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是指去諂媚當政者,當然就不對了。讚美不等於諂媚,所以,諂媚,無論如何都是不對的。但是,如果把他當作讚美,那就不一定了。讚美什麼,意思也就不一樣。我是把吳濁流這句話解讀為 不真誠的文學不是文學。
莊紫蓉11
可以請您談談愛情方面的經驗或是看法嗎?
吳 晟11
有關戀愛,我童年時有滿特別的經驗。這一部份我從來沒有講過,也沒寫過。我童年的故事滿多的,也滿奇特的,所以我打算明年寫一本童年回憶。現在你問起了,我就來談談。我國小四年級時就有一個女生寫信給我,信的內容大約是「想跟你做朋友」之類的。那時我就會寫所謂的情書了。後來她搬走了,也就沒再繼續通信。六年級時又跟另一個女生通信。在這方面,跟一般鄉下孩子比起來,我算是有滿特別的經驗。台大法律系教授黃宗樂是我學長,他常常說我國小時就很會談戀愛。其實就是寫寫信啦,這樣而已。
莊紫蓉12
您國小時就跟女同學有書信往來,家長或老師知道嗎?他們有什麼反應?
吳 晟12
這是很有趣的。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我國小四年級的老師,她是太認真的老師,非常好勝,什麼都要求第一,因為她自己本身非常優秀,是全國演講比賽第一名,所以她教我時也是要求非常嚴格。她那時候才18歲左右,有一次上課時發現我在寫信,她就說「不要臉,又在寫情書了。」現在想想真是很好笑。
| 吳晟先生著作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另一個是我父親的反應。以前我們寫信都會把信折成一個小方塊,每次我看完信之後,照樣折起來,用手巾把一疊信包起來放在褲袋裡。有一天早上,我換褲子時把那一包信拿出來放在桌上卻忘記放進新換的褲子的口袋裡面,等我到了學校才發現那包信不在褲袋裡,趕緊向人家借了鐵馬騎回家,卻找不到那包信了。我知道被我父親拿去了。隔兩天之後,我父親把那些信拿給我,問我「這女孩子是誰?」,我告訴他了,他說「嗯!寫得不錯。」這事就這樣過去了,也沒怎樣。因為我父親知道都是小孩子,沒什麼,而我讀書都是第一名,也沒有影響功課。我父親和老師的反應不同。
我這種事,當時大家都知道,也沒什麼。以前的孩子連牽手都沒有。就是寫寫信。
莊紫蓉13
您可能比較早熟。
吳 晟13
算起來是早熟。不過,應該說是那女生早熟,是她先寫信給我的。
莊紫蓉14
那時候您的心情如何?
吳 晟14
沒什麼啦。剛開始時有點不好意思。後來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心情,不過難免會對這個女生比較注意,對她比較好,彼此會互送東西。譬如她父親是警察,有很漂亮的十行紙,紙質很韌,可以拿來做踢鍵子,她會拿來送我。
長大後,我的學歷各方面都比她高,距離慢慢拉開了。雖然她還有意思來往,但是我的感覺已經不一樣了,不能合得來了。
莊紫蓉15
沒有那種感覺了。
吳 晟15
嗯!國小、初中、高中,有幾位有過來往的,都是這種狀況。那是年輕時的過程,我認識莊芳華以後才比較固定,過去小孩子時代的事就淡忘了。
莊紫蓉16
從國小到高中,每個階段都有 ──
吳 晟16
嘿嘿嘿!(帶點不好意思的笑)都有認識的。
莊紫蓉17
雖然不一定有很深的交往,但是那種感覺有時候會留存在心裡面。不是這樣嗎?
吳 晟17
不會呢。不會特別怎麼樣。因為接下來每個人有各自的際遇,各人過自己的生活。這方面我比較特別,我是屬於家庭生活的人,我每天都是歸人,是那種所謂的「愛家的男人」。所以,很自然的,我的家庭是我生活當中很大的部份。至於其他那些,我認為是年輕時候的故事,過去就過去了。現在想起來,也沒什麼不好,但是也不會特別去懷念。其實,是很坦蕩,把她當作一個曾經有過的還不錯的朋友。
日前我到台北演講,有人問我接下來要寫什麼。我說有可能會寫一本情詩。大家就很好奇地問我對象是誰。我說「要寫我太太啦!」,他們聽了就覺得沒什麼趣味。所以,這方面我是比較單純,我盡量避免複雜化。簡單說,是很保守的農村的,可以說是農民性格。
接下來我想談的是我的農民性格。因為我的農民性格很重,我很固定不愛變動,我愛做穡,我愛土地,我愛農作物,我愛田、我愛家、我愛太太,都是固定的,不會說有了太太還想怎麼樣。
現在大家很喜歡旅遊,我跟芳華說,每天我們都到自己的田園旅遊。這個觀念很不錯呢。旅遊,就是在認知、欣賞。而田地每天都不一樣,都在變化,其實,我每天都在我自己的田地旅遊。對太太也一樣,我每天都在跟她談戀愛,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情境。
我的農民性格,喜歡固定。固定不等於偏狹。一般人總認為固定就比較偏狹。其實是不一定的。走遍天下走馬看花又怎樣?對任何地方都沒有深入的瞭解,沒有情感。而我每天都在這個地方,我有我的情感,我對它的瞭解絕對不是來這裡晃一晃的人所能比的。同樣的,戀愛也是一樣,我的戀愛對像只有一個,我有每個階段不同的感受和體會。有人很多戀愛對象,可是沒有那個階段,他的體驗就不如我的深沈。不說深不深沈,起碼可以說這兩種體驗是不同的。因此,只能說體驗不同,不能說我的體驗比較偏狹。
很多人一說到寫農村寫土地,就認為偏狹,好像要走遍天下才開闊。我對這種看法很不以為然。走遍天下而都沒有深入的瞭解,那又怎樣?我對自己的家鄉一直參與其中,我看著它每個階段不同的變化。台灣的農村,土地的改變,人民價值觀的改變,我都在其中,我對這方面很熟,我的感情完全投入。有這樣的體驗,我可以對台灣農村有深入的描寫。
| 吳晟先生與莊紫蓉 於彰化溪州吳晟的田園 2000/7/11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我的農民性格,會讓一般人解釋為偏狹、格局小。其實我覺得不能這樣講,頂多只能說不同,而不能說誰比誰偏狹。你寫紐約我寫溪州,你的紐約就比我的溪州廣闊嗎?廣闊與否是看胸襟,是我的胸懷而不是我的所在地。任何人的所在地都一樣,你在台北市,你的所在地就是台北市,你不可能寫我的農村,那麼我也可以說你偏狹,台灣住那麼久,不知道台灣的農村,你怎麼那麼偏狹?我也可以這麼講。這是一樣的道理,你寫你的台北,寫你的眷村,我不會說你偏狹。可是為什麼你寫眷村就不偏狹,我寫農村就偏狹呢?你的台北市就是廣闊的,我的彰化就是偏狹的?這是簡單一想就清楚的道理。可是為什麼會變成大家很自然的講法。
莊紫蓉18
可能是因為沒有去深思,一般人都是依照既定的想法 ──
吳 晟18
對!你不能說我的生活體驗就是偏狹,你的生活體驗就是有國際觀。但是你們這些有國際觀世界觀的作家,有可能寫出台灣農村嗎?你們不可能寫也不肯寫台灣農村,我來寫,是因為我有我這些體驗,我的生活背景就是這樣。你只能說我寫得好或不好,而不能說我寫農村就是偏狹。如果我不寫台灣農村的詩,誰要寫?到目前為止,可以說我是寫得最多最完整的。
事實上,文學是根據各人的生活經驗、環境、文化背景,發展各人獨特的風格。我有我的背景,有我的經驗、文化背景,總合起來,然後我發展我的獨特性。文學創作,一定是先在地的,才能發展成所謂世界的。因為每個人都有立足點,不管你的立足點是紐約、台北或是溪州,這些立足點是不分大小的,都是立足點。任何一個文學家都是從他的立足點發展出來的。
莊紫蓉19
您的詩,尤其是早期,常常會流露出一種孤獨感 ──
吳 晟19
我想,孤獨感是共同的經驗,以我所知,每個人都有很大的成份是孤獨的。不管夫妻或是父子感情多好,每個人是個別的生命體,有很大的部份是獨立的。這個獨立的部份也就是孤獨的。孤獨是生命的本質很重要的部份。這都是共通的。差別只在於,有人一直書寫他的孤獨。我算是寫得比較少的,可能我下一本詩集會寫得多一些,因為比較老了,我會多寫一些生命本質的問題。我年輕時寫了很多孤獨方面的作品,可能那時候對社會上的事情沒有那麼瞭解。對社會事實瞭解越多,我的社會議題的詩就寫得越多,個人生命本質的就寫得少。社會議題的詩寫得多,就變成所謂的社會關懷。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面,只是你強化了哪一面,或者哪一面的比例比較大。我們生命中的孤獨、寂寞、悲傷,都隱藏起來,在日常生活中將這些感情內化了,放在心裡深處。譬如說雖然你母親已經過世十年了,你還是常常會去觸動,但是平常你不去想它,不去面對。我們的孤獨、悲傷都隱藏在心裡面,有人少寫社會議題,就會去寫這些。這是生命本質的東西,也沒什麼不對。像我,社會議題寫得差不多了,接下來想寫一些我對生命的體驗,比較屬於內化的東西。例如<雪景>這首詩,天地間的孤獨凝聚而成,事實上我們常常會有「天地之悠悠」那種感覺。這是很自然的感覺,差別只在於你有沒有用心去表現,表現出多少來。
莊紫蓉20
您《不如相忘》前面的幾篇以聲音為題的短文,是不是在探討生命的問題?
吳 晟20
這是我年輕時所寫的散文的一部份。年輕時我寫了不少散文,但是都沒有收錄。收在《不如相忘》的聲音小輯,我很喜歡,那是我年少的階段開始探觸生命的作品。我年輕時也寫了很多散文,在這本書裡收錄這幾篇,其中一個意義,就是留下這個記錄,在我的發展過程裡,並不是一開始就寫鄉土,其實也寫過很多這種所謂優美的文體,辭句很美,很有意象。第二個意義是,這些作品本身所表現的是我年輕時對生命的探觸。第三是,那些也有一點小傳的意思,譬如蟬聲寫我以前讀書時的情形,流浪的聲音寫出年輕時對流浪的追求。這些是較屬於對生命本質的探求。
莊紫蓉21
很多人都會去探討生命的意義。對人生的看法,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或是其他種種不同的態度。從年輕時候到現在,您追求、探觸生命的過程,每個階段有什麼不同?
吳 晟21
這是個大問題。其實我們剛才的談話已經有講到了。每個階段對生命的體會其實都差不多,也不能截然劃分,無法很具體地說明。事實上也是比例大小的問題。譬如說我高中的時候,改革社會的熱情幾乎佔滿了我生命的全部比例,那是我生命的動力,整個心思都是俠義精神。我高中時就被調查局詢問,大一時安全局來我家搜查。因為那時候社會議題佔了我生命的大部份,所以我不太會顧忌什麼。年紀漸大,開始對環境關注。回來教書、種田以後,對農村、土地、生態的議題特別關心。譬如我十幾年前寫的<苦笑>這首詩─大家欣賞稻穗讚嘆說「好美!」,而稻穗卻在苦笑「我吃農藥吃得好苦,你們卻說我好美。」。1970年代,我寫了很多植物,<木麻黃>是很典型的一首「我們是越來越瘦、越來越稀少的木麻黃」,那時我已經感覺到台灣的環境一直在改變。70年代,台灣的環境還沒有被破壞得這麼厲害,但是我已經感覺到農村的路樹一直減少。我關心的層面就放在這裡,我的心思大部分放在這裡。一直到現在,我對土地、植物、綠地等還是特別關心,甚至痛心。譬如我寫<憂傷西海岸>,整個海邊的木麻黃都被砍光了。有關山林、河川、土石流等等的作品,我也寫很多──「河川是你的血脈,山林是你的骨骼」,寫出了我的急切。1980年的<制止他們>,明顯地表現出我的著急,呼籲要趕快制止他們對環境的破壞。
講起來,我整個生命裡面,對社會關懷過度急切。我相信很少作家像我這樣不時都在為這些事情操煩。這是因為我的生長環境,我每天看著它的變化,而所看到的都是不好的改變,心裡就很焦急,寫出來的作品就沒辦法很優雅。可悲的是,就像<寫詩的最大悲哀>裡說的,即使心頭倘血,也要壓縮再壓縮,為了完成作品,必須忍住。如果我太急切,人家會批評說─藝術不能太急切啊。但是,急切難道不能是藝術的一種嗎?優雅瀟灑才是藝術嗎?這是一個重要的思辨。我沒有說你的雲淡風輕不是藝術,可是你不能說我的土地我的焦灼急切就不是藝術。不能說看不懂的才是藝術,清楚明白的就不是藝術。只能說是風格不同而已。
這些是目前台灣文學觀點很重要的思辨。
莊紫蓉22
講到文學美學的問題,我覺得很困難。以詩來講,什麼樣的詩藝術性比較高?我不瞭解。我讀詩只會覺得受到感動,其他的語言文字問題或是美學理論等等,就很難再進一步去分析了。您寫詩這麼久,對詩的美學方面有什麼看法?
吳 晟22
簡單一點說,我覺得感動是第一個條件。有的詩一讀就會受到感動,有的是開始讀的時候沒有感覺,越讀越有感受越感動。至於實在看不懂的詩,那就沒辦法了。還有一種詩是有趣味性,那也不錯。什麼是好詩?每個時代有不同的標準。經過一段長時間,大家共同認為比較好的就會留存下來,文學的過程就是這樣。不過,台灣的文學問題非常複雜,不是簡單幾句話可以解釋的,好壞的評斷不是純粹從作品本身來看,往往牽連到意識形態、時代背景,文學團體,文學的認知等等問題。譬如十年前沒有幾個人會講賴和,十年後的今天,不知道賴和會被人家笑。所以,對文學的理解或是文學的價值,有時候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甚至感情的寄託等等其他個人的因素也會影響對一篇作品的判斷,是很複雜的。因為時代越接近,越多那種非文學本質的因素,例如派別,屬性,都會影響對文學價值的判斷。不可諱言,台灣到目前為止,難免較容易注意到和自己同個文學團體的作家。或者社會上整個文化的導向,流行的就比較容易被注意到。所以,越近距離對文學價值觀的判斷越不單純,越容易牽涉到非文學本質的因素。
莊紫蓉23
這樣講起來,每年都有文學獎,評審時是不是也會牽涉到這些非文學的因素?
吳 晟23
是啊!以文學獎評審來講,評審之間的看法往往有很大的差異。甲評審認為很好的一篇作品,可能乙評審認為很差。所以選出來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這都需要再經過時間的篩選。
莊紫蓉24
也有可能很多好作品被埋沒了。
吳 晟24
有可能。好作家好作品被埋沒掉,這絕對是有可能的。人家都說,時間會證明一切,真理在時間的一邊。事實上,世間事是很複雜的,是非不一定那麼清楚,並不是好的就一定會留下來,或者一定就會有更多的讀者,還要看機緣等等複雜的因素。
講這些我沒什麼興趣,因為我是個寫作者,最關心的只有一樣,就是怎樣寫出更好的作品。至於有沒有受到肯定、聲名夠不夠等等,在意這些事情是很累的。一個創作者最重要的就是面對自己的作品,好好去做自己認為最好的表現。至於聲名多大、能不能流傳、有沒有得獎,都不在考慮之列了。我本來就不重視這些,現在越覺得那些不重要。我還是喜歡回到文學本題,更重要的是,希望寫出好作品。至於往後能不能流傳,或者能得到多少聲名,那對我的生活並沒有多少影響,稿費很有限,名聲也是如此而已,我每天去田里還更快樂。但是,你說我完全不在意那些,也不盡然。不過我會把大部分的心思放在田里、作品,以及身邊的人。
莊紫蓉25
一個作家想要寫,想寫得更好,這是發自內心的衝力。不過,寫出來還是希望有人欣賞吧?
吳 晟25
對啦!對啦!你講到我的重點了。實際上到現在有時候我還會想要出名,重點就是希望更多人能讀我的作品。我希望我所傳達的這些東西,有更多人來關心,譬如<憂傷西海岸>,希望大家關心海岸的問題,從我的作品裡面得到感動。親情的描寫是希望大家多關心親人。當然這是比較淺顯的一面,我在藝術上的追求是另外一面。我自己也有檢討,一本書所能獲得的版稅和稿費都很少,我不是靠寫作維生的,寫作不是為了利,這是沒話講的。至於名,希求聲名就是希望作品有更多人看,得到更多的回應與共鳴。我很希望我的書有人盜印,像善書一樣──敬請翻印,廣為流傳。這是很單純的想法。
莊紫蓉26
除了詩和散文以外,您嘗試過其他的文體嗎?
吳 晟26
我年輕時寫過小說,還有評論,包括影評,因為以前我很喜歡看電影。以前看電影時都有說明書(本事),我會把其中的好句子記下來。不過,主要的還是詩和散文這兩個文體。我覺得一個文體能夠寫好就很不錯了。在台灣,像我這樣兩種文體的產量都差不多的作家,也不簡單了。
莊紫蓉27
我看您的作品,覺得您對土地的感情很深,譬如<秋收之後>寫秋收之後的稻田「太累了─懶懶的躺著」。站在稻田的立場替稻田說出它的感覺。我覺得這很特別。
吳 晟27
你提起這點,我很高興。這又要說到我的農民性格。我看到土地,就會想到種作。我母親也是這樣,有時候出外坐火車經過稻田,一路上她所注意的都是作物,整個心思都在那上面。我一直都認為土地不能隨便毀棄,我親身參與過土質改良的階段。過去很多農地都是溪埔地,必須撿拾石頭,上堆肥。後來砂石車載來砂石,一下子就把這些經過幾代人的辛苦經營出來的農地毀了。我寫的<土地公>就寫這個景象,土地公發現那些砂石就是阿公阿祖他們撿拾起來的石頭啊,每一粒石頭都有我們祖先的血汗。只有像我親身經歷的,才能有這樣的體驗和感情。這不是光憑想像就可以的。
一般人講到土地,會想到一坪多少錢,這是經濟觀念。我不是這樣,看到土地,想到的是要種什麼。現在的人很輕易地就把土地用水泥築起來,這一來土地就死了。土地會吸收水分,會有作物成長,是有生命的。我看到的土地是有很豐沛的生命力。我一直覺得這樣的土地才是土地。現代人都把土地物化、商品化了,看到一塊地就想要蓋什麼。當然,我並不是說我們都不能蓋房子、不能建設,我的意思是我們必須很慎重的規劃。我們台灣在這方面很弱,整體的國土規劃都沒有好好做,一些財團,以經濟導向對土地一再加以毀損。今天台灣的山林、海邊所以會變成這樣,就是這樣來的。譬如南投一帶,必須封山一百年,地質才能穩定下來。這是太輕易破壞的結果。
| 吳晟先生著作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海岸也一樣,亂挖,接著就是土地下陷、鹹化等種種問題都來了。至於平原,僅有的一塊綠地,馬上加以開發。現在農地釋放了,卻不加規劃。以後台灣的居住品質將越來越差。因為有這樣的憂心,所以我會一直講這些事。後來我發現講這些問題很沒有趣味,年輕人沒有興趣聽這些,台北人也不感興趣,不浪漫不美啊。我在文藝營講這些,大家都沒什麼興趣。那些過客心態的人,可以講得很唯美。其實我也可以講那些五四三的話──我們要用愛要寬容,用自在的心情過生活。這種話很容易講,也不是不對。但是這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有愛就會有恨。不要說恨,我不會恨,我是著急。因為我愛這個地方,我才會著急啊!我只是表現我的著急而沒有說出我的愛,其實從我的著急就能夠體會我的愛。而你只說出你的愛而沒有說你的著急;你只說你的寬容而沒有說你的痛恨。沒有是非的寬容是什麼寬容?不斷在傷害又不斷在寬容,我覺得這樣會混淆了。我不是要發展仇恨,也不是要計較,我們要去制止那些傷害的行為。他殺人害人,沒有悔悟,也沒有接受制裁,我們就說要寬容他,有人罵他一句,大家就說要寬容嘛。這實在是笑話,我們台灣社會竟然變成這樣。譬如一個人危害了別人,至少他應該反省,是非要講清楚。這些都沒有,你不能莫名其妙就在講寬容啊!再談到整個台灣社會的問題,不能用寬容、愛這麼加以簡單化。破壞了台灣的山林,引發土石流,造成那麼大的傷害,對這些政策和行為,還一直說要寬容。我不是不懂愛和寬容,我比較急切的是不希望這些事情再發生。可是這樣大家就認為我的心胸比較狹窄。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太浮面化了,而沒有深入去探討,因為一般人都不太喜歡用頭腦。
莊紫蓉28
講到對土地的看法,土地是有生命的,您所體驗到的土地生命力是什麼狀況?土地怎麼表現它的生命力?
吳 晟28
正常的土地,隨時會成長,它上面有作物。甚至你不必去理它,也會有各種不同的生物在它上面生長。例如你剛才提到的<秋收之後>,秋收後的稻田寬闊的躺著,接下來我說 有野花野草任意開放。不必種作,自然有很多豐富的物種繁衍,你會覺得很美。所以我很喜歡看秋收之後的稻田,那種景像有點感傷。稻子已經收割了,稻草燒一燒,撒一些菜籽,茼蒿、白菜、油菜﹑A菜等等,不久就長得很茂盛。沒有撒菜籽的地方,它會自己長出各種花草,充滿生機。這種感覺和水泥地有很大的差別。另外,小孩子在泥土地上跑跳摔都沒關係,不會受傷。而在水泥地上,小孩子是經不起摔的。
莊紫蓉29
在人和土地的關係上,譬如人會不會過度種植,讓土地太累了?
吳 晟29
以前農業社會比較會過度種植。現在則有農藥和化學肥料過度使用的嚴重問題。這都會傷害土地,必須改變。現在有些農人慢慢地不用化學肥料,改用以前的堆肥。挑肥清豬糞,都是我以前做過的事。
可能大家要慢慢改變耕作習慣,盡量不要使用化學肥料,盡量不用農藥。我現在種作就不用農藥,像除草,一般農人都用除草劑,我們買了一個割草機來割草,不用藥劑。這種觀念,將來會越來越普遍。
莊紫蓉30
現在您的家鄉,大家對這種觀念接受的程度如何?
吳 晟30
目前還很少人接受。不過,從知識份子開始推動,大家慢慢會接受。可能還要經過一段時間。
莊紫蓉31
新的國中國文課本收了您的一篇散文<不驚田水冷霜霜>。您有什麼意見?
吳 晟31
這一篇當然不錯,可以看出早年台灣農村辛苦的景象。不過,很多老師都覺得不好教,對秧子、稻子都不瞭解。其實我同意用這一篇,有一個非文學的念頭,就是想藉助這篇文章喚起大家的共同回憶,共同來瞭解台灣農村早期的發展過程,這也是我農民性格的表現。我用老師普遍反應較好的<負荷>來換這一篇,卻得到不好教的反應。我的詩換下來,覺得有點可惜。
莊紫蓉32
最好是兩篇都上去。
吳 晟32
那是不可能的。還活著的作家有一篇被選進去就很不錯了。
莊紫蓉33
如果教育政策全面改過來,或許有可能。
吳 晟33
現在民間版的也有各人的看法,高中課本選我的文章並不多,也多半是偏向過去國立編譯館所編選的文章。國中版的開放十幾家,哪一家要收我的文章也不知道,說不定人家不收我的文章。
莊紫蓉34
您在經營一首詩或一組詩,和經營一畦稻田,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吳 晟34
這很難講。不過有一點,芳華都說我寫字好像在刻字,一筆一畫地刻得很整齊。我種田也是很仔細。這是我的個性,做每件事都很仔細。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命情境,人的一生各有不同的成長背景,文化涵養。不同的個性、環境,塑造成不同的作家。我是比較順應生活軌道的人,我就是在這樣的軌道裡,接受它,認真生活,然後從我的生活裡發展我的文學。我不是刻意去追求什麼或是刻意要表現什麼的人。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譬如從小讀書,就這樣一路讀下來。畢業後有機會到台北當編輯,但是我母親一個人在家,我放心不下,剛好有機會回來教書,我就回來了。回來後,我叫芳華也請調回來這裡教書,然後結婚生子,承擔整個家庭的責任。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今年我退休了,剛好我母親過世留下了一些田,兄弟分了之後,我哥哥人在美國,不可能回來耕種,我就把他的部份買下來。我弟弟不要種那麼多,我也把他的一部份買下來。其實我是貸款來買這些田的,但是只能這樣做。我跟隨著母親種了幾十年的田,我捨不得在母親過世不久就把它賣掉。這就是農民性格。
我這樣的生活體驗,沒有刻意去追求什麼,我只是一個順應生活者。
| 吳晟先生與莊紫蓉 於彰化溪州吳晟的田園 2000/7/11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35
您是順應生活沒錯。但是您好像有個生活的基調,那個基調或許可以說是您對親人,對家庭,對土地的愛吧?!
吳 晟35
謝謝你這樣的詮釋。實在是這樣。我不是藝術性格的人,我是農民性格。譬如80年代去愛荷華時,看看也覺得沒什麼,我一直想回來。我所牽掛的是學生、親人、土地。我身邊的人,我有機會關心,有能力幫助,很自然地去做。這樣的農民性格,比較踏實,能做什麼就做什麼,也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譬如《店子頭》那本書裡有一篇<一枝草一點露>,寫一個鄰居小孩從小沒有母親,每天黃昏跟著一群鄰居的孩子來我家的院子玩。天暗之後大家都回去了,她還不離開。我們問她為什麼不回家,她默默地不回答,我妹妹就添飯給她吃。第二天,她又在那邊,我就知道她沒飯吃。後來探聽得知她沒有母親,父親浪蕩不顧家。我們就照顧她。這小孩就變成好像我們家的孩子一樣。後來我太太生了孩子,那時她上小學了,下課之後會趕緊來幫忙我們照看孩子。我想,她覺得能幫一點忙,心裡上比較平衡舒坦。我們也把她當作自己的孩子,買衣服給她穿,芳華幫她清理頭蝨。直到現在我們還有來往。這件事就是這麼自然,碰到了,剛好有能力,就這麼做。否則我們也沒有能力愛盡天下所有的人。事實上,以我的個性,我很能體會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盡蔽天下寒士」的心情,我對很多人很自然地會有惻隱之心。而能做多少,其實是很有限的。我們很願意愛很多人,但是真正能「愛到」的真是很有限。
所以,後來我很怕學生,因為學生那麼多,我能幫助的其實很少。我發表在《自由時報》的一篇<青青校樹>就是寫我退休的心情,意思是愛與寬容是需要力氣的,也就是需要行動。我們看到很多問題,但是卻沒有力氣幫忙或改善。有時候這也會造成很大的心理負擔。
農民性格可以說是貫穿我一生的主要基調,順著生命的步調,不刻意去做特別的追求。我對我的學生、家庭、土地,都用心追求經營。我的追求就在我的生活本身。
莊紫蓉36
這是您的選擇。
今天聽您講的這些,感覺就像您的詩和散文一樣,很平實動人。
吳 晟36
我的詩就像土地,它不會喧譁,不會製造事件,不會引起媒體的注意,它沒有浪漫。我的文學觀也是這樣,實實在在地寫在我自己的土地上旅遊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