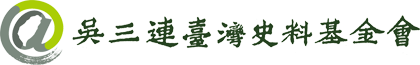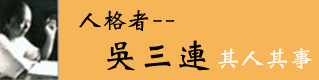痛苦的救贖──宗教與文學
 |
時 間:1997年06月11日
|
杜潘芳格女士是台灣著名女詩人,1927年出生於新竹新埔。創作以詩為主,日治時代以日文寫作,戰後嘗試用中文創作,近年來則寫了不少客語詩。曾獲得第一屆陳秀喜詩獎。
| 杜潘芳格女士 陳秀喜作品討論會 1998.11.01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1
今天很高興來到杜潘芳格女士中壢家中,請杜潘女士談談影響您最深的宗教信仰,以及文學創作。
杜潘芳格1
就從三十年前那場車禍談起吧。
三十年前,我和我先生發生一場車禍,那件事對我影響很大。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我們去淡水打高爾夫,傍晚坐計程車回來,在關渡附近和得利奶粉老闆的座車相撞,對方是外國製大車,一點都沒有受影響,我們坐的計程車,被撞得轉了一百八十度,司機和我先生飛到車外,我在車內,頭上破皮流血。當時我只記掛著我先生,趕緊出來找他,看到司機坐在地上沒什麼大礙,我先生則受傷很重,大家建議將他送到榮民醫院,但是我主張送去中山北路的馬偕醫院,因為我弟弟在馬偕醫院當了很久的醫生,那時雖然已經離開馬偕自己開業,但是還有很多熟識的醫生在。那時正好有一輛載焦炭卸了貨的卡車經過,我就拜託司機載我們到馬偕。到了醫院,照了片子,發現他的肋骨斷了好幾根,刺到肺部,不停地流血。我公公趕來醫院,醫生告訴他要準備棺材了。
當時我最小的兒子才小學三、四年級,他下面還有一個妹妹,我想,假如我先生走了,我們怎麼辦?我恐怕必須去替人家燒飯洗衣,才能撫養子女。於是我不斷地禱告,祈求上帝讓我先生好起來,我一定會全心做神的義工,向一向最迷信的客家人傳教。後來經過四十幾天的治療,我先生終於漸漸好起來了。
| 杜潘芳格女士, 二二八事件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攝於國家圖書館,1997.02.20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以後,我一有時間就到新竹、後龍、苗栗、中壢等客家人居住的地區,做傳教的工作。有一段時期,我的腳痛得很厲害,行動困難,但是我一定參加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一的客家人活動。有時回來中壢下了火車,腳痛得不能走路,在車站的的椅子上休息很久才慢慢走回家,就這樣七年都不間斷。我先生退休後,有時和我一道去傳教,他會開車,就不必走太多路,我腳痛的毛病也好了。但是,向客家人傳教很困難,他們大部分信一貫道,不太歡迎我們去傳福音。
這次車禍發生時,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生命的脆弱,一剎那之間,身體就受到那麼大的傷害,甚至可能生命就這樣消失。感謝神的恩典,使我先生得以康復,我們還能過安定的生活,這之後,我的信仰更加虔誠堅定。
莊紫蓉2
台灣很多老作家,日治時代用日文寫作,戰後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必須重新學習中文,這是「跨越語言的一代」較吃虧的地方。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一輩的作家,戰前懂日文,戰後又學會中文,加上自己的母語──客家話或福佬話,而語言的背後是思想與文化,他們懂得較多種語言,不知不覺就吸收了多種的文化,使他們的思想更開闊,更有深度,這又是他們佔便宜的地方。對這一點,您的看法如何?
杜潘芳格2
你說的很對,我想,懂多種語言,思想會多元化,無形中,在那些不同的語言文化的磨擦當中,會自我批評、自我要求,就像金字塔,底部的根基很深厚,可以將金字塔築得很高。例如陳芳明懂英文,在美國吸收歐美文化,張良澤在日本,日本人將各國的各種作品翻譯成日文,他就藉著日文吸收了很多國家的思想文化。
你這個觀點很新,一般人都以同情的眼光來看這件事,只看到自己的東西被拿走,事實上,我們也得到很多東西。尤其是日治時代對日語的訓練非常徹底,用日語可以表達很深刻的東西。現在我用客家話、北京話講不出來的事情,都可以用日語表達,我的「倉庫」裡面有很多日語的語彙,隨時可以取出來應用表達各種感情和思想。所以,我用北京話寫作,有時不能確切地表達出我真正的想法,宋澤萊同情我、就勸我用日文寫,他說,現在翻譯的人才很多,請他們翻譯就可以了。
但是,我心裡又認為應該用自己的母語寫作,於是寫了一些客家詩,如果我再用日語寫作,可以嗎?我們看看世界上,有很多像台灣一樣的情形,例如波蘭、羅馬尼亞,被俄國、德國或法國先後佔領,他們的作家,有時用俄文、德文、法文……寫,有時用他們的母語寫,這應該是沒關係吧!就這樣,我一直猶疑不定。
莊紫蓉3
現在台北市有三所高中被選定為試辦第二外國語的學校,我們學校(陽明高中)也是其中之一,今年有法語、西班牙語和日語三種語言班。所以,下一代懂各種外語的人會愈來愈多,將有更多人能接受外文作品。
杜潘芳格3
不久前,日本有一個團體,主持人金美齡女士帶一些日本人來台灣,慶祝李登輝總統就職一週年,他們主張國粹主義。
現在有人認為,世界是個地球村,應該不要分國家、民族。在這個觀念下,大家不必太計較一定要用什麼語言,不管是福佬話、客家話或什麼語言,會使用哪種語言,就拿出來使用,不要太狹隘。但是,主張國粹主義的另一派,又有不同的說法。目前台灣人對李登輝先生的想法有不同的意見,也是從這兩個不同的角度出發的。
|
楊千鶴與杜潘芳格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這個觀念來看我寫作的語言問題,在邏輯上我還沒有辦法說服自己,不知道怎麼辦。一方面我告訴自己:學會日語,是命運,因為時代因素,讓我多學了一種語言,這是「賺到了」。而我的「倉庫」裡已經儲存了那麼多的日語語彙,只有用日文寫作,才能表現出我的思想,就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作家一樣,儘可以使用自己最熟悉最拿手的語言,沒有關係。但是另一方面,心中仍然有矛盾和衝突,不知道要怎麼做,心裡才不會有矛盾,才能真實地面對自己。我是使用日文最流利,但是,有時我會想,日文是日本人的,有日本人的精神,我是客家人,我是台灣人,為什麼我
要用日文?這樣是不是會很怪?邱永漢和陳舜臣用日文寫了很多作品,我看了之後就會想:語言是溝通的工具,用什麼文學寫作似乎沒有很大的關係,但是,語言背後的思想就不是那麼簡單了。日本奈良天理大學學生井關えつこ為了寫畢業論文,曾經來台灣訪問我,她寫的〈語言的細胞〉一文中提到,語言是靈,是精神上的細胞,一直使用某一個國家的語言,就會被感化,變成那個國家的人。日治時代皇民化運動,要台灣人改姓名,說日語,很快就能夠將台灣人同化,因為日語當中就有日本人的精神。
莊紫蓉4
您小時候接受日本教育,學會日本語,和日本人接受日本教育,說日本話,在思想上有怎麼樣的差異?
杜潘芳格4
小時候,我在家裡都講客家話,去學校才講日語,當時學校裡禁止講母語、有時候我不小心說了客家話,就很怕被人家聽到,怕受到處罰。這種情形和戰後在學校裡只能說北京話,禁說母語的情形一模一樣。不過,我小時候在家裡都講客家話,我身體裡面的「客家人」並沒有死掉。後來接受二十年的日本教育,再接受很多外來文化,這些外來的東西和我本身的客家精神,兩者的份量必須相等,當我的某種想法,只能用日文表達時,就用日文寫,而裡面仍然能夠保留我原本的客家人精神,這時,日語只是我借用的工具而已,我自己有堅定的立場,不會動搖。我想,在這種情況下
,使用日文應該沒有問題。
另外,報告、論文之類的文章,或是宗教方面的經典,像佛經、聖經,語言就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可以透過翻譯傳達到世界各處,超越國籍、民族等,同時也超越時代。
| 杜潘芳格女士 《陳秀喜全集》發表會 攝於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講到宗教,有人說宗教是共同的幻想,神是人造出來的神話,是一種迷信,人死後就什麼都沒有了,而宗教則說,人死後還有靈魂存在,像這樣,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我的看法是,宗教是對自己的要求,我、杜潘芳格是客家人,從小在家裡就講客家話,上學之後在學校講日語,戰後我在家還是講客語,而寫作、寫日記、寫信繼續用日文,有人把我的作品譯成中文。後來我也嘗試用中文寫,但是我的中文很幼稚,只有小學三、四年級的程度。所以,第一屆陳秀喜詩獎評審時,白萩就指出詩是最精緻的文學,語言很重要,他認為我的詩,文字上不夠精粹。但是李元貞和李敏勇他們卻認為,即使如此,但是我的詩,在樸拙的文字當中,會閃現出一絲光芒,就像魚游在水中,遇到光線照射,魚鱗閃出亮光一樣。在他們的堅持之下,我才得到第一屆陳秀喜詩獎。
莊紫蓉5
我很喜歡您寫的<荒原>,那首詩裡說,「映在疾駛的車窗的眼/重疊的農作物和延綿的民家卻像一無事物的荒原」那疾駛的車窗,象徵時間快速地流過,一剎那之間,「青青的草原,遠遠的山,河水的細流,綠綠的田園」都成了「一無事物的荒原」,做為大自然一份子的人,天天為生活、為名利,為種種目的而忙碌不休,直到死亡的那一天,這一切都成空,「無為蠕動的人群」在時間的疾流中,也將化為一片荒原。這首詩讓我們想到生死、人生意義的問題,最後一句「蒼白而悲哀的綠色荒原呵。」荒原是什麼都沒有,但是卻是「綠色」的,其中又隱含生機,在死滅當中有再生的可能,有限的生命仍有成為永恆的可能,仍帶有一絲希望。
杜潘芳格5
這首詩是我有一次坐在車裡面,往外看,忽然眼前的景物都變成一片荒原,我眨眨眼再看,那些景物又回到眼前,我就把這個經驗寫成〈荒原〉,倒是很少人提到這首詩。
莊紫蓉6
有一段時間,您曾經教授插花,補貼家用,請談談當時的情形。
杜潘芳格6
日治時代,必須有執照才能教授插花,而執照的取得很困難,有時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才能拿到執照。
莊紫蓉7
您是婚後才取得執照嗎?
杜潘芳格7
是,我教插花有七年的時間,那是結婚以後了,婚前我在娘家生活很優裕,嫁到杜家,生活很苦,我先生有四個弟弟、五個妹妹(後來二個妹妹送人,剩三個),孩子太多,負擔太重。
|
杜慶壽、杜潘芳格夫婦 |
 |
莊紫蓉8
我覺得您很浪漫,不會太現實,而願意嫁給貧窮的杜醫師。
杜潘芳格8
這也不是單純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從小看到父母親的情形,影響我對婚姻的看法。我父親本身對祖國有很大的憧憬,但是又被日本人重用,經常和他們喝酒,又不能說出心裡的話,非常苦悶,他回到家裡就會打我媽媽,性格變得很怪,不說話,也不吃飯。我母親是基督徒,黑白分得很清楚,要求自己要堅持原則,他們兩人的個性都很強,經常吵架。我是長女,下面還有三個弟弟、三個妹妹,父母都無暇關注我的事,我要期末考試時,留了紙條在桌上,結果父母都沒有看。母親要照顧那麼多弟妹,有時還要我幫忙,她看到我在看小說,就罵我說:「看那麼多書有什麼用,全世界各國的小說多的是,看也看不完。」父親則心裡一直十分苦悶,一喝酒回家就發洩。所以,我十七歲以前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莊紫蓉9
您這樣的的童年生活,對您以後造成什麼影響?
杜潘芳格9
對我影響很大。小時候,我父親很疼愛我,帶著我和母親去日本留學,我六、七歲時才搬回來,父親一個人留在日本。後來父親寫信要母親去日本陪他,當時除了我和大弟外,母親肚子裡還懷著妹妹,祖父只答應母親帶著弟弟及肚子裡的妹妹去日本,父親又一定要母親帶我去。母親心裡很苦,從很高的地方跳下來,希望造成流產,就可以帶我去了,結果還是沒有流掉,母親只好帶著弟弟和未出世的妹妹到日本去。後來母親告訴我,當父親在日本碼頭接他們時,看不到我,非常生氣,掉頭就走,讓母親帶著弟弟,拖著行李在後面追趕。
當時我跟著大家到基隆碼頭,以為我也要一起去日本,結果我卻被留了下來,那種被丟棄的感覺到現在還留著。之後,我就跟著祖父母和大我一歲的叔叔一起睡、一起生活,我對祖父母不敢像自己父母那麼親,有一次我們到台北,我那個叔叔看到店裡掛著一件大衣,就要祖父買給他,當時六、七歲的我心裡想:「那是女孩子的大衣,我來穿不是很好嗎?」但是我不敢講。祖父就買給他,也沒問我要不要。我和小叔叔一起上學,在學校裡沒有叫他叔叔,他回來就會向祖母告狀,說我沒有禮貌,祖母就罵我,那時我心裡就會感覺,為什麼祖父母沒有平等地對待我?
我童年時的這些痛苦的事,對我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響,以後我對人比較容易懷疑,根據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得到充分的愛。後來我信基督教,宗教給我很大的安慰與力量。
莊紫蓉10
宗教紓解了您心中的痛苦,寫作是不是也有這個作用?
杜潘芳格10
對,寫詩對我來說是很大的紓解,把心中的苦悶,用文字寫出來,就感到輕鬆多了,寫日記也是很好的方法,我從十幾歲開始寫日記,到現在七十一歲了,都沒有中斷,如果沒有寫日記,我會瘋掉。女人結婚後,和來自不同家庭,性格脾氣不同的丈夫,多少都會有磨擦衝突,我和杜醫師結婚五十年了,有時候感覺彼此還是不大瞭解,吵架也是很難避免,這樣的難關要如何突破?我在〈鴿仔的聲〉這首詩裡說:「我感覺三界無家…」,我現在住的房子是我先生的,而我母親住在我弟弟家,我也不能去住,我女兒都是和公婆同住,我也不能去,我好像沒有家一樣。
這些痛苦,光靠寫作是無法完全消解的,必須很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化解痛苦,對我來說,宗教還是最重要的。
幾年前我看到一篇日文文章,談到有限的生命體──人,如何面對無限的、絕對的神(或其他無限的東西)。那篇文章說:「在人生的旅途,人知道自己經常是處在不安的狀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因此,人總是缺乏自信,有時會懷疑自己是在做秀嗎?故意討人喜歡嗎?是不是虛假的?人必須覺醒,瞭解自己實在很軟弱,必須要謙卑,不要驕傲,相信有那絕對的,可以依靠的神,就像嬰孩對父母的信靠,在母親懷抱裡,什麼也不怕。這是人類的宗教信仰。」反過來看,信了神以後,神不是人造出來的神話,是人對神完全信靠,在神面前謙卑為懷,感謝神創造萬物,讚美神,這樣,神就會愛世人。聖經裡記載著:「神愛謙卑的人。」我們愈來愈謙卑,和神愈來愈接近,直到死亡,什麼也不用怕,即使人死之後沒有靈魂也沒有關係,在我有生之日,已經得到神的照顧,七個子女都孝順我,母親還在,又有那麼多好朋友。信仰帶給我喜樂與平安,這是寫作不能達到的境界,以前,胡適先生提倡以藝術文學,用美來代替宗教,李元貞教授就曾經寫文章表示我們應該採用胡適的這個理論,我就在台灣時報寫了一篇文章反駁,我認為宗教是無可代替的。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
莊紫蓉11
李敏勇先生在<誕生在島上的一棵女人樹>裡談到,您的詩,「是在抒情裡包容著思想的詩」。您詩作裡的思想性,主要是來自宗教吧?
杜潘芳格11
宗教對我的影響太大了,如果沒有受到神和聖靈的感動,我的詩也寫不出來,並不是想要寫就能寫。
莊紫蓉12
除了宗教之外,您也看了不少哲學方面的書,哪些哲學家對您的影響較大?
杜潘芳格12
我是看了一些哲學家的著作,但是很難說受到那位哲學家的影響較大,以前看過斯賓諾沙的書,後來有一段時期很醉心於叔本華所說的人生幸福三條件:強而有力,智慧和運氣,不過,我的宗教信仰也會改變我的哲學觀。
莊紫蓉13
哪些作家或作品對您影響較大?喜歡看那些書?
杜潘芳格13
目前我還是對宗教方面的書最感興趣,文學作品方面,有時會看看大江健三郎的著作,不過,他的作品不容易讀。中學時,我喜歡看《飄》、《大地》、《傲慢與偏見》、《小婦人》等等世界名著,小學時則看《小公主》、《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等。《格林童話》裡有一個故事,我現在還有深刻的印象,那個故事說,有兩個女孩去取水,其中一個好心腸的好孩,潑灑出來的水都變成小鳥等可愛的動物,另一個壞心腸的好孩,潑出來的水則變成蟑螂之類可怕的動物。那時我就想,我要做好心腸的女孩。
莊紫蓉14
您除了寫詩之外,也寫過小說,請談談您的小說。
杜潘芳格14
我曾經想當小說家,寫過幾篇小說,但是以前台北三省堂的老闆,說我較適合寫詩,不是小說家。第一篇小說是〈繭〉,鍾肇政先生看過,說我寫得很好,但是人物太少,那是我三、四十歲時寫的,記得當時我寫得很勤,每天都寫。後來這篇小說不見了,怎麼找都找不到,非常可惜,這一篇是中篇小說。第二篇〈給L的信〉,為了應徵日本百萬小說獎而寫,大約有四萬字,後來沒有得獎,稿子退回來了,現在還在我手邊。第三篇〈月桃花〉也是長篇,把我的童年經驗和日本長崎被原子彈轟炸的事寫進去,那是我在美國五年之間寫的。這篇小說去年被日本天理大學教授下村作次
郎拿去準備出版,後來沒有出版。
| 杜潘芳格著作書影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15
您的作品,杜醫師都會先看嗎?他會不會提供意見?
杜潘芳格15
我寫的詩,他都看過,其他的就不一定,有時候他也會提出他的看法。
莊紫蓉16
鄭清文先生說過,中國文學作品很少直接描寫聲音,大都是像「大珠小珠落玉盤」這種抽像的描述。我現在正在學日文,看到桃太郎的故事裡,有很多聲音的描寫,例如洗衣服的聲音、桃子漂過來的聲音等等。您的詩<網球>裡「巴達,巴達,當球網一搖晃,」<日曆>裡也有「颯一聲/今天又被撕破的/日曆」這些聲音的描寫,這是受日文影響,用日文寫作的緣故嗎?
杜潘芳格16
對,日文有很多形容聲音的語詞,另外,形容詞也很多,我有一首詩,其中一句「ひよろ ひよの」很難翻譯,意思是很長、很高,風吹會搖動,不太穩定的樣子。
現在我有時候會想:我真的不能寫小說嗎?三島由紀夫自殺前寫的散文或小說,裡面有很多的詩,可以把它看作散文詩,我想,做一個詩人小說家也可以吧?
莊紫蓉17
詩和小說是不是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作者要表達的思想,或是要說的道理,都是藏在裡面,不直接講出來?
杜潘芳格17
這一點是一樣的,只是在創作時,詩用較為簡短的文字表達,也許醞釀的時間很長,但是寫出來的則是精簡的。
我以前寫過小說,很想當小說家,那時每天寫得很認真。現在我想我寫不出來了。
從小我就愛好文學,我想,這一點和我父親有密切的關係。
我父親雖然是讀法律的,但是愛好文藝,學生時代陸續買了不少文學名著,世界文學大系,像《雙城記》、《基督山恩仇記》等小說,我在父親的書櫥找到不少文學作品來看。另外,父親還買了一套漢文的《資治通鑑》,還有杜甫、韓愈、白樂天……等人的作品,這些書籍在父親去世之後,都給了我,我想,我的文學細胞是來自於父親。
莊紫蓉18
您小時候住在新埔,您對童年住的故鄉有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杜潘芳格18
有啊!我那首〈小山〉就是寫童年的地方,現在我還留著一張相片,我採了一把野薑花,和家人在小山前照的。日本幾位教授來台灣時,就曾經去過新埔我的老家,他們要去看看我筆下的那座小山,也想看看夕陽下的白鷺鷥飛過天際的情景。我小時候住的老家還在,被政府列為古蹟,現在有個年老的族人住在那裡照顧。
莊紫蓉19
您在讀書時代,曾經受到那幾位老師的影響?
杜潘芳格19
我就讀新竹女中時,有一位國語(日語)老師安田先生很疼愛我,他要回日本時,把他的藏書都送給我。後來我到台北就讀女子高等學院,那是二年制的學校,教女孩子插花、洋裁、茶道等等,有時會從男子高等學校請來教授講授歷史或和歌等文學,一口氣上課三、四個鐘頭,考試時常常出一個大題目,讓我們盡量發揮,例如〈德川家康的鎖國政策〉或〈煤炭〉這樣的題目,我總是長篇大論寫得很高興。校長大森先生建議我到日本京都專門學院讀文科,但是當時戰爭時期,來往台灣和日本間的船經常被魚雷炸沈,我就沒有到日本去。
莊紫蓉20
去年五月,台灣師範大學春季駐校作家李喬先生在師大演講,他說:「人生是痛苦的,人生也是無意義的,惟一的意義是想辦法減少人生的痛苦。」對他的說法,您有什麼看法嗎?
杜潘芳格20
就我個人而言,十七歲以前,在家裡有很多痛苦的經驗,在學校又常受到日本小孩欺負。結婚之後,一方面要幫助丈夫診所的業務,家裡人口多,負擔沈重,再加上夫妻之間的衝突磨擦,我想人生是痛苦的。每個人紓解痛苦的方法不一樣,也可能不止一種方法,對我來說,宗教是解除痛苦的最重要方法,其次是寫作,而宗教信仰是來自於我的母親,她本身是虔誠的基督徒,文學則得自於父親的影響,他喜好文藝。宗教和寫作,紓解了我大部分的苦痛,但是,我覺得真正的痛苦,還是要靠活生生的人才能解除,親情和友情才是減輕痛苦的重要力量。
| 莊紫蓉與杜潘芳格合影 陳秀喜詩獎頒獎會上 1997.05.03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
感謝您接受訪問,讓我們對您的宗教信仰和文學創作有更深的瞭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