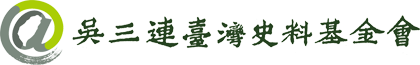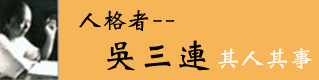在文學與歷史之間--專訪許達然
 |
時 間:2001年11月12日 9:00~11:00am 地 點:東海大學圖書館藝文中心貴賓室 |
在台南圖書館成長
莊紫蓉1
首先請您談談您出生的地方—台南市。
許達然1
我家是在台南市最繁華的地方,我爸爸是做生意的,週遭環境很吵,因為沒有讀書環境,我小學五年級開始,晚上愛跑到台南市圖書館,讀書之外也會借書來看,就這樣對文學發生興趣。
莊紫蓉2
您小學五年級就會去圖書館讀書,通常小孩子都是愛玩—
許達然2
當然也跟我的性格有關係,我不大會玩。所以,只要我在台南,大部分時間都在圖書館,包括我唸東海,暑假回去時也是。所以,就亂看書,興趣很廣。那時候我覺得歷史包羅萬象,就唸歷史,我是第一志願進東海的。
莊紫蓉3
您小時候在圖書館看書,是什麼書都看?
許達然3
主要是王雲五編的萬有文庫、世界名著。那時候台南圖書館從日本時代開始就收集了很多書。
| 第24屆吳三連獎贈獎典禮 吳三連獎文學獎得主許達然 2001年11月14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4
您當時看的書,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
許達然4
有,貝多芬傳、雪萊傳等等,萬有文庫有的我都看,不一定看得懂,也不一定都看完。後來唸東海時,我的興趣也是西洋史,當時我跟隨楊紹震先生,還有從師大來東海兼課的王德昭先生。我當助教的時候才對中國史有興趣。
莊紫蓉5
為什麼轉變興趣?
許達然5
那時藍文徵教授跟我講,他說﹕「以後你要有一點成就的話,還是要研究中國歷史。」他覺得對於西洋史,我們只能教,要研究的話是比不過西洋人的。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我想,我是台灣人,就研究台灣史吧。本來我對台灣史也看了一些,但是還沒真正去研究,在當助教時才決定研究台灣史。那時有個美國教授來東海教西洋史和美國史,我當他的助教。他是研究中國史的,有一些英文寫的有關中國史的書,我向他借來看,覺得人家研究得非常好。就這樣,我研究的興趣從西洋史轉到中國史–其實,我要研究的是台灣史。到美國,我博士論文就寫台灣史,這在當時是很少的。
莊紫蓉6
那時候研究台灣史,在台灣的資料怎麼樣?
許達然6
他們都沒有用檔案,不那麼嚴謹,很令人失望。曹永和先生是例外,他很嚴謹,直接用荷蘭的檔案。
賣燒餅的老兵
莊紫蓉7
台南是一個古老的城市,您童年住在這麼一個地方,有什麼特殊的記憶?或是讓您感受深刻的事情?
許達然7
是有一些。因為我沒什麼娛樂,所以都早睡早起,假期時早上五、六點,我經常騎著腳踏車到台南市的忠烈祠,看看英文書,背背英文。那時有個退役軍人在賣燒餅,他的燒餅是放在一個桶子裡的。我跟他買燒餅,那是我的早餐。我心裡想﹕他們當兵,之後流落到台灣,覺得人世間的遭遇令人感嘆。唸東海時,我也參加工作營,開始有一些社會意識,同情生活上比較沒有受照顧的。可是有這麼一種感覺,就是都沒有做任何事情。不過,以那時候的環境,事實上也不可能做什麼事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就讀東海大學,假期回台南時,開始對台灣,對社會關懷。不過這講得遠一點啦,小時候當然沒有這些。
| 第24屆吳三連獎贈獎典禮 吳三連獎文學獎得主許達然 2001年11月14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8
不過小時候觀察到的一些印象,可能會留在潛意識裡。
許達然8
也可能,那我就不知道了。
莊紫蓉9
剛剛聽您講您小時候去圖書館看書,都是一個人?有沒有跟同伴、同學?
許達然9
我幾乎沒有什麼朋友。
莊紫蓉10
兄弟姊妹呢?
許達然10
兄弟姊妹也很少有什麼 communication。我父母做生意很忙,我最大,回家有時候要照顧弟妹,但是除了以哥哥照顧小的以外,沒有什麼特別的像別的家庭那麼親密的感覺。
莊紫蓉11
有些做生意的家庭需要孩子幫忙。
許達然11
我倒沒有,因為我爸爸請了一些人幫忙。
莊紫蓉12
您父親是做什麼生意?
許達然12
他是鋁具、五金的批發商,很忙,每天從早上十點忙到晚上十點。人家來訂貨,他就送貨。有一輛卡車,送貨到南台灣各地。我家經濟環境不錯。
莊紫蓉13
您母親幫著做生意?
許達然13
我母親沒做什麼,就是傳統的家庭主婦。
莊紫蓉14
過去有些家長會要求孩子讀什麼,您父親沒要您讀什麼嗎?
許達然14
我爸爸不會強迫我什麼,我是比較幸運。我說要進東海念歷史,他沒有反對。
莊紫蓉15
那真是幸福。您母親還在哦!?
許達然15
對,我等一下就要回台南看她。
莊紫蓉16
年紀很大了?
許達然16
81歲。
語言、音樂、文學
莊紫蓉17
您小學時有受到哪個老師的影響嗎?
許達然17
有。有一個鄧正宗老師對我非常好,我六年級時叫我去他家一起唸書。大概我功課還不錯,他覺得我還可以。不是每天都去,一個星期去他家兩三天,不一定唸什麼書。他是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他是我小學時最值得懷念的老師。
莊紫蓉18
您中學時就開始寫作了?
許達然18
對,老師說我可以投稿,那時台南有個叫做《青年天地》的刊物,是救國團的。第一篇寫什麼,我忘了。我高一時,應徵《新新文藝》徵文,得了首獎。
| 許達然作品 《同情的理解》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莊紫蓉19
得了獎也是一種鼓勵。中學時您還是繼續看書哦?!
許達然19
對,從小學五年級一直到出國,只要我人在台南,我都會跑到圖書館看書。
莊紫蓉20
葉石濤先生也說台南圖書館的書都被他看遍了。
許達然20
就是那個圖書館,我出國以後,那圖書館拆了。
莊紫蓉21
好像藏書很豐富。
許達然21
台南圖書館的書很多,日文書恐怕更多。中文書大部分是以前在中國大陸出版的。
莊紫蓉22
中學時,有沒有像小學時對你那麼好的老師?
許達然22
有,國文老師,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三的老師張芳廷,他是東北人,也是國大代表,他對我很好,給我很多鼓勵。我唸東海時,他過世了。
莊紫蓉23
東海的回憶更多吧?
許達然23
對,因為我在東海待了七年。因為我眼睛不好,耳朵跟鍾老一樣不是很靈光,所以不用當兵,一畢業我就留在學校。我很感謝楊紹震老師,大四的時候,有一天,他問我畢業以後要幹什麼,我說我不知道,他說那你就留下來,他知道我不用當兵。(大三升大四時那個暑假要上成功嶺受訓,我不用受訓,就跑到台北震旦補習班補習德文。那時東海沒有德文課,我是跟黎烈文學了法文。唸完德文回台南之前我先回東海,碰到楊老師,那時他就知道我不用當兵。)所以,畢業後我就留下來。後來我才知道,他特別跑去跟校長講,因為那時歷史系已經有了兩個助教,夠多了,他特別幫
忙,吳校長也答應,我就這樣又在東海三年。我特別感激楊教授,他在兩年前過世了。他有沒有教過妳?
莊紫蓉24
有。
許達然24
那三年間,開始覺得有的書看不到,所以就決定出國。本來不是要出國的,也是運氣好申請到獎學金。
莊紫蓉25
可能您的成績滿好的。
許達然25
對對,成績不錯。英文也考得不錯,因為我搞西洋史,英文還可以。
| 許達然作品 《含淚的微笑》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莊紫蓉26
您學法文、德文是為了—-
許達然26
因為那時對西洋史有興趣。
莊紫蓉27
也學日文嗎?
許達然27
日文是到美國以後,在哈佛才學的。在東海,那時候有一個老師教日文,我的感覺是國民政府不鼓勵人家學日文,我大四時才有日文課,而我那時候正在學法文,也是因為我那時的偏見,要研究西洋史,所以就沒有學日文。很可惜,早應該學日文。
莊紫蓉28
看您的作品,感覺您對語言很敏感,也特別注重。您學這麼多種語言,可能對這方面有幫助嗎?
許達然28
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是英文的影響,因為外文比中文嚴謹,中文的文法鬆散。我寫作用字,嚴謹是不敢說,不過,至少覺得不必說的話就不說。
莊紫蓉29
而且好像很多意含。
許達然29
對,我覺得語言也是一種象徵,就儘可能讓它的意含多一點。
莊紫蓉30
所以我覺得看您的詩或是散文,都沒辦法看很快。而且不能只看一遍,每一次看,感受都不一樣。
許達然30
對對,所以我知道我的讀者很少。
莊紫蓉31
我感覺您不是很愛說話的人,可是您作品裡面語言的精密,對語言的掌控卻那麼好,這讓我特別感興趣。
許達然31
我是不會說話。
莊紫蓉32
不是不會說話,是比較寡言。我想,語言和音樂有關係,您喜歡音樂吧?
許達然32
我是很喜歡音樂,古典音樂,其他的我不能講。對音樂不是懂,是喜歡聽。
莊紫蓉33
那時候東海有音樂廳。
許達然33
就在銘賢堂那邊。
莊紫蓉34
我大學時在音樂廳工讀。
許達然34
真的?那是很好的工讀。妳工讀了幾年?
莊紫蓉35
三年。
許達然35
也是在銘賢堂?
莊紫蓉36
不是,在藝術館。
許達然36
哦?那時候改到藝術館了?我們那時候是在銘賢堂旁邊學生中心樓上一個小房間。
莊紫蓉37
您從小就喜歡音樂嗎?
許達然37
真正聽音樂是到東海以後。
莊紫蓉38
那時又有音樂課。
許達然38
對,許常惠和鄧昌國教我們音樂。許常惠教三個星期,鄧昌國教兩個星期。
莊紫蓉39
您喜歡貝多芬?
許達然39
我是最喜歡貝多芬的。
莊紫蓉40
貝多芬的作品很耐聽,而且有一股力量。您的作品,雖然有的是寫一些人物的悲慘境遇,可是
其中好像有積極的力量。
許達然40
是嗎?
生命主題
莊紫蓉41
您有一篇作品把人生比做小提琴,有主題和技巧。就您個人而言,您人生的主題是什麼?
許達然41
我一向都這麼認為,也不敢說一向,不過至少從東海那段時期以後,就領悟到,要自己活得好,一定要在別人也活得好的環境下才能夠。別人活得不好,自己心裡就不會舒服。所謂「別人」也包括動物。所以,在台灣每次看到流浪狗就受不了,心裡會很難過。
莊紫蓉42
不過要別人活得好,不是那麼容易。
許達然42
是啊!事實上不可能,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所以自己不會很快樂。自己很有限,自己能夠做得好的就盡力去做,我研究台灣史,就把台灣史盡可能寫得好一點,創作也盡可能,其他就沒辦法。心裡的感覺一直是這樣,這個世界太不公平,太多人,甚至太多動物——
莊紫蓉43
有時候我會想﹕這個世界最後都是要毀滅的,我們做什麼、爭什麼有用嗎?有必要嗎?
許達然43
我覺得爭都是沒什麼必要的。可是這個世界大家都在爭。
莊紫蓉44
然而人活著,也不能就這樣白白活著啊!人生的「主題和技巧」,如果說技巧是生活態度、生活方式,您的生活方式是怎樣的?
許達然44
我的生活非常單調,沒什麼特別,也很少社交,幾乎沒有社交。沒有什麼情趣,唯一的情趣大概就是聽音樂。
莊紫蓉45
您對這樣的生活—-
許達然45
不會覺得不好,很清靜。大部分都在家。
莊紫蓉46
這樣跟家人會比較親密哦?
許達然46
對。
莊紫蓉47
我還是對您作品裡面的語言運用感興趣。您開始寫作時,就對文字特別注意?
許達然47
對,也不敢說特別,很注意語句的表達,儘可能把不必要的字刪掉。
莊紫蓉48
那是中學的時候嗎?
許達然48
是到東海以後才這樣的。我現在反省一下,可能跟英文有關係,不過我也不敢講。中學時還沒有,那時糊里糊塗寫,唸東海以後才開始有意識要—也不敢這麼講—建立自己的風格。
莊紫蓉49
您可能是受到外文的影響,不過基本上您是用中文創作,您對中文的文字有特別下過什麼工夫嗎?
許達然49
好像沒有,不過寫的時候會注意儘可能用最少的字表達,可是我又不喜歡用成語,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莊紫蓉50
為什麼不喜歡用成語?
許達然50
因為成語已經是一個不能讓人思考的語言,我們接觸到成語就會直接想到那固定的含意。我中學時就不喜歡用成語–創作的時候。有時候兩個字可以表達,成語一定要四個字,而且成語跟時代脫離關係,比方車水馬龍。中文特別多成語。
莊紫蓉51
您也常用押韻的字。
許達然51
對,儘可能運用中文字的特色,外國文字沒有的。
自認為台灣人是一種很自然的感情
莊紫蓉52
您有一篇文章講到聲音,剛剛您提到您的聽力不是很好—
許達然52
對,從小大概是中耳炎,聽力不好,又近視,所以不用當兵。那時候不當兵我還很失望,因為
我一向沒有在一個很苦的環境,所以想去鍛鍊鍛鍊。不過後來我還是當了兵。我當了一年助教以後
,就想出國,楊教授要我留下來。我就想,兩年以後就出國。我當完助教一年就去考留學考,那時
還有留學考,本來當助教不用考留學考就可出國,我去考留學考是為了要去當兵,那時候男孩子沒
有當兵不能出國,所以我是很少數為了當兵而去考留學考的。考上後我向學校請假,到政工幹校受
兩個月的思想訓練,那時也要我參加國民黨,我都找藉口拒絕。受訓完之後變成少尉,可是我沒有
馬上出國,我又回來當助教,所以我受兩次教育召集,到成功嶺兩次。
| 第24屆吳三連獎贈獎典禮 吳三連獎文學獎得主 台北國賓飯店 陳郁秀(左)、許達然(右) 2001年11月14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53
早期很多人加入國民黨,您為什麼不加入?
許達然53
我以「對政治沒什麼興趣」把他推掉了。
莊紫蓉54
那時候對國民黨會有反感嗎?
許達然54
對,覺得國民黨太專制了。我想,大家都會反感,只是不敢講出來。有人入黨,因為在政府機關做事,也沒辦法。我自己不願意加入,可是我對加入的人沒有任何怪罪。
莊紫蓉55
那是當時的時代背景。您很早就想研究台灣史,和台灣意識有關係嗎?
許達然55
我覺得學歷史,自己是台灣人,所以就想研究台灣史。
莊紫蓉56
那時候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許達然56
我那時候不這麼認為,我沒有任何省籍偏見,在我求學過程中,對我很好的很多老師都是外省人。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族群偏見,更不用講省籍了。坦白講,在東海時,我覺得我是台灣人。
莊紫蓉57
我們一向受的教育都是說我們是中國人,很多人不會去反省,我也是這樣,沒有特別去思考。
許達然57
因為在這個地方生長一定是台灣人啊。
莊紫蓉58
這樣應該是很自然的。
許達然58
是啊,那時候外省同學有時候會說﹕「你們台灣人」。台灣人,對我來講是很自然的層次,是一種感情,也是意識的層次。「台灣人」這個東西,恐怕在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已經形成了,覺得自己是屬於這裡,我是這麼想。
不合作的台灣人
莊紫蓉59
您研究台灣史是哪一方面?
許達然59
因為我比較喜歡社會學,所以研究台灣社會史。
莊紫蓉60
台灣人到底是什麼樣子,是很多人在探討的問題。鍾老的《台灣人三部曲》試圖要塑造台灣人的形象。您從台灣社會史的角度來看,從古到今,台灣人的性格有哪些變化,或是有哪些性格是不變的。
許達然60
這很難講。我覺得台灣人—在這個土地上的、包括1949年來台灣的—都不合作。從清朝就這樣,福佬和客家械鬥,福佬的漳州原籍的和泉州原籍的械鬥。不但不合作,還互相對立、攻擊,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這很奇怪。這也不是先來後來的問題,譬如福老和客家幾乎是同時來的–我們都認為客家晚到台灣,其實不一定–,日治時代也一樣,也是都不合作才會有文化協會分裂,現在也一樣,這是不是跟台灣人的性格有關,我就不知道了。
| 許達然作品 《人行道》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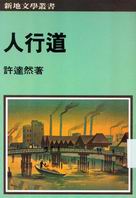 |
莊紫蓉61
包括1949年來台灣的也是這樣?
許達然61
對啊,所以才會有外省情結和本省情結,愈搞愈糟,就是不合作。以前是武鬥,現在是文鬥。
莊紫蓉62
這,原因是?
許達然62
假如是清朝,還可以說是爭土地或是族群的情結或者語言不通。現在大家語言應該通了,至少有一個共同的語言,還是這樣。這是台灣歷史發展的悲劇。
莊紫蓉63
過去有一種說法﹕台灣人不團結、愛錢、怕死,您覺得是這樣嗎?
許達然63
我覺得台灣人倒是很懂得冒險,祖先是這樣嘛,有冒險精神,現在還是這樣,你看很多台灣人到中國大陸做生意。怕死?也不一定,台灣人一直都有反壓迫的傳統,事實上是充滿了冒險精神。因為閩南人和客家人都很有那種另外找天地開拓的精神。
莊紫蓉64
原住民好像滿勇敢的。
許達然64
對。我唸東海的時候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實現去山上住一段時間的期望。他們是最可憐的一群,什麼都沒有,還受歧視。一直到現在,政府都還沒有照顧他們。現在他們只剩下45萬人了。
台灣生病了
莊紫蓉65
最近幾年常常有人說台灣生病了,您是不是也這麼覺得?
許達然65
事實上很久了。
莊紫蓉66
病徵是什麼?
許達然66
為什麼住在這個地方都沒有群體的觀念,都是為自己在爭,有人爭權,有人爭錢,卻一直沒有一個整體的觀念,假如連這塊土地都沒有了,那還爭什麼?
莊紫蓉67
這跟教育有關係嗎?
許達然67
我真的不知道。一方面是不合作,一方面是各爭各的。
莊紫蓉68
講到台灣的問題,目前經濟很被重視。您曾經到英國研究經濟社會史,您看經濟在人類的歷史上,是佔很重要的地位吧?
許達然68
對,就是馬克斯那一套。在思想方面,我是比較傾向社會主義,一個政府能夠照顧那些資源比較少的人。現在共產主義是整個垮了,垮的原因當然很多,其中極權是一個因素。極權就形成一個很大的官僚體系,根本就沒有真正在照顧老百姓,怪不得它會垮。英國那種福利國家的系統,重稅,也可以說是一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妥協的一個產品,當然也有問題。美國,到現在都還沒有全民健保,台灣有全民健保,是相當不錯的。一個社會要達到公平是不可能,至少要一個有社會良心的社會。
| 許達然作品 《吐》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當年接辦《台灣文藝》的鍾肇政、陳永興,很有膽量
莊紫蓉69
您和鍾老什麼時候認識?
許達然69
1965年第一屆青年文藝獎,在中央日報領獎。鍾老從龍潭來。在會場,他自己過來跟我握手。那時我很感動,他對台灣的文學那麼執著,我只是個小孩子,他那麼看重我。就這樣我們認識了。我也在那一年出國,所以一直沒有連絡。直到吳濁流先生去世,他辦《台灣文藝》,我在美國替他跑腿。1980年國建會,我們同一組—文化組,國建會那一年開始有文化組。
莊紫蓉70
您覺得鍾老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許達然70
他一直提攜後進,這是相當難得的,他跟葉老都一樣。這是值得我們這一輩人學習的,我們也應該提攜後進。他對台灣文學的執著,很可佩,不只鍾老,葉老也是,不管環境多壞。鍾老花很多精神、時間為客家文化努力。—這次不知道有沒有時間去看他。
莊紫蓉71
上禮拜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去板橋幫蘇貞昌助選。
許達然71
哦!他有幫人家站台?不管怎樣,作家一定要參與,不能只是寫。
莊紫蓉72
這好像是你一向的想法。
許達然72
對,可是就做不到,只能夠寫寫。
莊紫蓉73
至少用寫作關懷社會。
許達然73
嗯!鍾老那時候接《台灣文藝》,也是要很有膽量。1970年代後期、1980年代後期的環境,主持《台灣文藝》真的是要有膽量。以後陳永興接辦,都要有心裡準備。
莊紫蓉74
您跟鍾老有書信來往吧?
許達然74
有,鍾先生寫給我的信相當多,可是—
莊紫蓉75
您回去以後找找看—
許達然75
好,我回去會找。不過那時我們信裡談的大部份是關於《台灣文藝》,有訂戶,我把錢寄給他等等。
莊紫蓉76
那時候《台灣文藝》在美國的狀況怎樣?
許達然76
看的人並不多,即使有人訂也不一定看,等於是間接贊助。當時,就是要花一些精神去拉訂戶,找朋友。
把「台灣文學」當作一個名詞來用,始於「台灣文學研究會」
莊紫蓉77
那時候有個「台灣文學研究會」?
許達然77
對,是我們搞的,1982年,我一直有這麼一個想法﹕台灣文學在台灣,這四個字或是這種東西在台灣,政府不准,我們在美國還不做一點事的話,真的是對不起台灣文學,所以我就去組「台灣文學研究會」,有幾位朋友參加。剛好那一年,1982年,楊逵到美國去,他到愛荷華,也到我家住了一些日子,我跟他提到這個,他很贊成,說﹕「卡緊哩,卡緊哩。」所以在他回台灣時,我們就在洛杉磯成立。
| 許達然作品 《土》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莊紫蓉78
您覺得台灣文學研究會有產生什麼作用嗎?
許達然78
我覺得沒有什麼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有這麼一個組織。現在回想起來,假如說還可以留下一些什麼的話,就是把「台灣文學」這四個字當做一個名詞來用。現在台灣文學是一個大家所能夠接受的,在那個時候是有它的——。每年開一次會,請台灣的作家去,也許是另外一個作用。
莊紫蓉79
有凝聚台灣人的作用嗎?
許達然79
呃!沒有,在美國完全沒有。
莊紫蓉80
外國人知道有這個研究會嗎?
許達然80
我想他們不會知道吧?!這是我們自己台灣人–我們這個研究會也有一兩個外省人,我本身就沒有省籍偏見—在辦,對洋人是沒有什麼影響。
以西方文學社會學的理論研究台灣文學
許達然80
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我1983、84年在台灣,83年那個冬天,台灣大學代聯會之類的社團舉行一系列演講,也邀我去,我就講台灣文學社會學。那時候任何演講都要訓導處通過,訓導處、中文系、外文系,加上文學院長來看,中文系有一個人反對,他說我這個人有問題,說我罵過餘光中。這是亂講,我從來沒有罵過餘光中,事實上我也從來沒有罵過人。他的意思是我不能去講。訓導處也可能認為有「台灣文學」這四個字不適當。那時文學院長王曾才是我的朋友,他說,許文雄這個人沒有問題。這個演講就通過了。但是訓導處認為「台灣文學」這四個字不恰當,要我改,我
不改,所以在台大演講的時候就錄了音。
我講這個是,1983年底,還是有這個情形。所以是在困難的環境下—
莊紫蓉81
他們錄音,後來沒怎樣吧?
許達然81
沒有,沒有怎樣。王曾才相當不錯,學問和人格都好。我很久沒有跟他連絡了。
莊紫蓉82
我上過他的課,那時候他到東海來兼課。
許達然82
對,那時我當助教時,他從劍橋大學回來,來東海兼課。我跟他很談得來。
莊紫蓉83
您那次演講台灣文學社會學,內容是講什麼?
許達然83
主要是以西方文學社會學的理論用在台灣文學的研究。
莊紫蓉84
那時候在台灣好像比較少做這樣的研究?
許達然84
對,因為我比較喜歡理論性的東西,社會學的東西我讀了很多,就想把社會學或者文學社會學帶到台灣的文學研究。那時我是講這個,一些理論的東西,用台灣文學做例子來證實。可是在官方認為「台灣文學」這四個字不妥。
莊紫蓉85
您舉的台灣文學的例子是小說嗎?
許達然85
都有哦?!詩比較少,恐怕多半是小說。
莊紫蓉86
之前我訪問過陳千武先生,他強調現代詩的自由民主獨立的現代精神,但是他認為台灣文壇比較重視小說而不重視詩。
許達然86
好像是這樣,不只台灣,任何國家都這樣。
莊紫蓉87
不過我有個疑惑,小說是不是也可以表現現代精神?
許達然87
我想小說應該更能夠表現現代精神,因為詩比較間接啊。如果是現代主義的詩,是能夠表現現代精神。不過,外國的現代主義的詩,是保守的,像艾略特,Ezra Pound龐德,他們都是很保守的,這就很奇怪,他們的詩是要打破傳統,要寫都市人的失落感,都市人的那種dislocation 放錯地方的感覺,可是他們的意識形態是非常保守的,用比較政治的話來講是跟時代潮流是相反的,這很奇怪。所以你看Ezra Pound,他同情法西斯,艾略特他是思想保守、性格保守,這不知道怎麼去解釋。只有少數像奧登,他寫現代主義的詩,他的思想是激進的。
莊紫蓉88
所謂保守和激進—
許達然88
就是說,艾略特表現出來的現代主義,可是他的整個意識形態、整個思考卻是往過去走,接受權威。現代主義應該是反任何權威,可是,除了創作以外,他們是接近權威,或者鼓勵人家接近權威。龐德是最極端的一個例子,同情法西斯,在歐洲他廣播,後來美國判他刑,因為這是叛國罪,他很倒楣。後來很多人替他陳情,他晚年是在精神病院度過的。
陳千武先生指的可能是現代詩,不一定是現代主義的詩。
莊紫蓉89
他是說台灣現代主義的詩沒辦法發展,因為政府不准。所以他說台灣直到現在還在發展超現實主義的詩,而那種超現實主義是超脫現實,跟西方的超現實主義不同。
許達然89
對,對,這是真的。超現實主義事實上也是相當反抗性的,對現代文明的批判。這個,台灣超現實主義沒有做到。
| 許達然作品 《水邊》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莊紫蓉90
就人類思想上而言,文學是不是走在前面?
許達然90
那就看從什麼觀點來看,假如那個作家寫作的思想傾向不是寫實主義,是超越現代的,可能會有。不過,寫作基本上從現實出發,去想像。超現實意味著不滿現實,解放想像。西方有些超現實作家後來都相信社會主義。但台灣的超現實詩人卻幾乎都是反動的。
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
莊紫蓉91
有人說,文學比歷史還真實,您研究歷史,也寫詩寫散文,對這個您的看法如何?
許達然91
其實歷史是一種解釋,在這方面文學和歷史可以連在一起。真正發生的歷史我們看不到,即使看到,每個人對那個歷史發生的解釋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所唸的歷史都是解釋,既然是解釋,一定要用文字,在這方面它跟文學是一樣的。既然歷史是一種解釋的話,今天對某一件歷史事件的解釋,明天也可能不一樣,你對某一件歷史事件的解釋,也可能跟我不一樣,因為我們的想法不一定一樣。所以歷史不是絕對的,或者可以說,歷史主觀的成份很高。可是我們一談到歷史,就以為歷史不能改。沒有這種東西。比方吳鳳的事情,以前他是那麼崇高偉大,現在我們對吳鳳這個歷史的解釋又不一樣,覺得他根本就欺負原住民。其實,兩者都是解釋,對某一件事情文學的解釋,或對某一件事情歷史的解釋。但是,歷史不像文學想像的空間那麼大,例如發生在桃園縣的事情,不能把他想像為台中縣。文學就可以這麼想像,明明是發生在台中縣,可以想像成,或者解釋成發生在台北縣。
用寫詩的心情寫散文
莊紫蓉92
您的散文和詩很接近,有時候不容易分—
許達然92
對,因為我一直認為詩和散文沒有什麼不一樣,除非我們寫的散文是論述性的,那就不一樣了。假如是創作性的散文,我想跟詩是一樣的。至少我是這樣做,寫散文的時候,我一直把它當作詩在寫。
莊紫蓉93
您寫散文的時候會不會把它當作小說來寫?
許達然93
也是希望這樣嘗試,可是自己能力有限,做不到。
莊紫蓉94
我看您有幾篇散文像小說一樣。
許達然94
是希望這樣做,可是自己不一定做得到。因為小說比較難寫,小說要有故事。不過,當然現在有人講小說不一定要有故事。我又喜歡簡潔,所以就沒辦法寫小說。
莊紫蓉95
不過您有幾篇散文也是有故事。
許達然95
對。一般是把散文當作聊天一樣。我是不願意這樣做。
莊紫蓉96
在東海的那七年,您的創作是不是比較多?
許達然96
對,在東海寫得比較多,而且那時候寫完後沒有改就投稿,現在回想起來是很可怕。有一段時期,寫了就給《中央日報》,因為那時候可以投的地方不多。孫如陵主編,他很快就登出來。
寫作是痛苦的;不寫更苦
莊紫蓉97
好像滿多作家認為寫作是痛苦的—
許達然97
我也是這麼覺得。一定想要表達什麼才寫,這個思考過程應該是痛苦的。
莊紫蓉98
因為有東西想要寫才會寫,感到痛苦是不是表現上的問題?
許達然98
表達出來以後就會覺得比較好一點。不把它表達出來恐怕會更痛苦,不過在表達的思考過程當中,還是覺得痛苦,並不是表達不出來。
莊紫蓉99
您寫作是有一些東西觸發,然後才寫嗎?
許達然99
大概是這樣。
莊紫蓉100
可能有些是很久以前的?
許達然100
對,可能是以前的一些事情放在腦裡,可是沒有馬上寫,後來才寫。
另外,我不願意寫自己,這是我個人的偏見。當然以前小時候是寫,因為小時候世界有限,以後就不願意寫跟自己有關的,這可能跟一般的散文不大一樣,他們多半是寫跟自己有關的,我是盡量避免跟自己有關。是不是因為跟學歷史有關,我不知道。因為自己沒什麼好寫,哈哈!
莊紫蓉101
或者是跟您對文學的看法有關。不過,自己也是社會的一部份,—
許達然101
所以多多少少會有自己在裡頭。
受中國文學作品的影響不深
莊紫蓉102
您閱讀的文學作品當中,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
許達然102
坦白講,文學作品我閱讀不多,閱讀較多的可能是在台南圖書館那段時期,或者在東海唸書回台南那時期。後來我就很少唸文學作品了,理論的倒是很喜歡唸。你是指中國的或外國的?
莊紫蓉103
都有。
許達然103
哦!都有的話,當然是唸了一些,不過跟別人比起來,算是少的。英文的詩我倒是唸很多,不管是以前或現代的,不過跟別人比起來,文學作品我唸得並不多,我到了美國才唸《紅樓夢》。所以,恐怕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不深,很慚愧。
莊紫蓉104
西洋的作品唸得比較多?
許達然104
對,小時候是唸翻譯本,後來就直接唸原文本。唸文學的少,也可能是因為學歷史的時候唸歷史的書比較多。不過在芝加哥大學唸思想史的時候,倒是唸了不少文學的東西,我老師 Krieger,在美國相當有名。我記得唸19世紀歐洲思想史,20世紀歐洲思想史,文學的東西唸得不少,老師要我們唸Dostoevski的兩本小說。20世紀思想史的時候,除了塗爾幹,韋伯外,我們也唸《似水年華》、湯馬斯曼,卡謬,還有沙特的戲劇,那我倒是比較喜歡,他也要我們唸一些哲學的,我就似懂非懂
從疏離到孤獨
許達然104
日治時期以來的台灣文學、當代台灣作家的作品,我唸了很多,而且很認真唸,因為想研究。
莊紫蓉105
小說、詩都唸?
許達然105
對,長篇、短篇都有。我曾經用英文寫過從台灣的文學創作—主要是小說—來看台灣的疏離感,二十多年前寫的,在德國出版,曾經翻成中文。
莊紫蓉106
您那篇論文有沒有引起什麼反應?
許達然106
沒有啦。是一種我理想中的文學社會學的習作,所以我從當代小說來看台灣的疏離感。疏離是一個幾乎可以概括現代人的一種心理感覺和社會現象。以前在德國提出疏離是說,我們人創造神,然後神來控制我們,所以我們就疏離了我們的本性。也就是說,我們被我們的創造物所控制。後來馬克斯把這疏離的概念弄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工人製造東西,但是他卻享受不到他所製造的東西,他拿到的是工資。所以,工人,也就是創作者,跟他的產品就有了疏離的感覺,不能直接去享用。這是疏離的一方面的解釋。台灣的疏離更多了,政治上的疏離。知識份子有疏離感,是因為他所期望的跟現實有差距。當他的期望跟現實有差距時,知識份子--其實也是任何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就會有疏離感。西方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家有一個解釋革命的理論,覺得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疏離感。比方中產階級有錢以後,得不到政治的權力,他就疏離,所以要去爭,法國革命可以用這個解釋,台灣的民主運動,也可以用這個去解釋。這當然是一種解釋,比較廣義的疏離。我那篇論文不是政治性的解釋,是社會學或是經濟的解釋。
| 第24屆吳三連獎贈獎典禮 鄭清文(左)、許達然(右) 2001年11月14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107
疏離感是最近二、三十年來講得比較多,可是,是不是從有人類以來就有疏離感?
許達然107
照理應該是這樣。尤其台灣的社會在經濟社會的轉型--那時候應該還沒有政治的轉型,還看不到政治的遠景--這種疏離感就會特別多,幾乎所有的人都有這種疏離感。疏離感怎麼表達?作家替他們表達。作家寫的時候也不一定有「疏離」這個概念,可是他描寫出來的可能是這樣,所以我就從那些作品抽出來討論。
莊紫蓉108
那時候您討論到的是哪幾位作家?
許達然108
現在都忘了,工人方面,我當然是用楊青矗的啦,還有鄭清文、李喬、黃春明、王拓,我舉的例子都是鄉土作家,–也不一定,像王文興的《家變》,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觀念上的疏離,兒子欺負爸爸。所以不只是鄉土作家。
莊紫蓉109
您覺得疏離感這種疏離的現象,或是這種感覺,在現在的社會是不是越來越嚴重?
許達然109
應該是吧,現在轉型比二、三十年前更厲害。所以還可以用疏離這個名詞去套。
莊紫蓉110
這樣的話,對人的精神會造成什麼樣的—
許達然110
很大的,我們現在每天面對機器,當然我們會很高興e-mail等等,可是我們面對的是機器,人跟人就疏離了,我們跟人談話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是跟機器談話。我們假想我們是跟人談話,透過機器,這疏離感會越來越深,越來越嚴重。而且在資本主義化–全球化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化,資本化就是商品化–,人際關係疏離會越來越深,因為人會把另外一個人當作是剝削的對象,所以關係會越來越物質化,疏離感會越深。
莊紫蓉111
這樣,人會越來越孤獨。
許達然111
是。
莊紫蓉112
那會不會回到原點,我覺得人本來就是孤獨的。
許達然112
對,齊克果說,孤獨的時候才感覺存在。
莊紫蓉113
講到孤獨,您寫作的時候是不是孤獨的?
許達然113
一定是孤獨嘛,而且現在社會一定是這樣。德國Walter Benjamin 就認為小說是近代西方社會孤獨的產品,因為在小說以前是tale--故事,在小說以前的tale的時期,是一個社區的產品,寫的人他唸給社區的人聽,他寫的都是群體的經驗。小說一定是近代的,小說一定是孤獨的產品,寫的人在家裡寫,唸的人也是在家裡唸,不是當眾朗誦。所以到了近代以後,任何文學的創作都是孤獨的而且孤獨也一定是小說的內容。現代社會世人把上帝踢出他的領域。當然所謂踢出,並不是說他不上教堂,而是神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可以控制一切。在一個上帝死亡的世界裡頭,什麼都可以做,也什麼都孤獨。所以,孤獨不只是創作的情況,也是創作的內容。匈牙利的盧卡齊認為近代小說的內容是人的孤獨世界,這個世界是被上帝所遺棄的。
| 許達然作品 《遠方》書影 圖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
 |
莊紫蓉114
孤獨的時候也可以很自由。
許達然114
對對。
莊紫蓉115
孤獨的時候,思考會比較活潑一點?!
許達然115
這也是為什麼存在主義都會追溯到齊克果。以前在18世紀理性時代,笛卡爾不是說「我想所以我在」?到了19世紀浪漫主義起來,浪漫主義覺得「我感覺所以我存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自然主義起來,自然主義是一定要觀察人的社會,「我觀察所以我存在」。後來存在主義又代替自然主義,「我存在,所以我想、我感覺、我觀察」。我存在這個存在,假如按照齊克果,那是孤獨才會去想,才會去感覺,才會去觀察,芸芸眾生常常是觀察不清楚。
| 東海大學 許達然 2001年11月12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在東海找到愛情
莊紫蓉116
請您談談在東海和夫人認識的經過,以及和其他好朋友交往的情形,好嗎?
許達然116
我當助教時她大三,那時我們才開始做朋友,這也是為什麼東海是我最懷念的地方,不只在這邊唸書,而且找到–找到她。嘿嘿!她相當不錯,有獎學金以外,她還工讀,她工讀四年。我1965年出國,出國前我們訂婚。
莊紫蓉117
我覺得東海是很適合戀愛的地方。那時候校園很安全。
許達然117
而且大家都很樸實。
莊紫蓉118
對。夫人是淡水人嗎?
許達然118
對,所以我們在家大部分講閩南話,小孩–我有兩個壯丁–會聽閩南話,他們跟我們講英文,我跟我太太都講閩南話。
莊紫蓉119
您在東海有沒有比較特別的回憶?
許達然119
其實也不特別。你那時候的圖書館是—
莊紫蓉120
舊的。
許達然120
哦!我上課以外都在圖書館混。圖書館晚上十點關門,我回來宿舍刷牙就睡了,我早睡早起。早起在校園到處逛,那時候都是相思林,不那麼高,覺得特別有情調。我很少下山,我大一的時候只下山過一次,那時候我家火燒,1958年台灣最大的火災,我家附近都燒光了,我看到報紙才知道我家火燒。
莊紫蓉121
您不喜歡下山?
許達然121
對,沒有什麼意思啊。若下山,主要是去看電影,或是去中央書局的二樓看書。通常我晚上喜歡在圖書館,有時候在文學院唸書。那時的總務長是畢律斯,是個美國人,好像沒有結婚。我不知道東海要省電,跑到文學院一個小教室看書。有一天晚上,突然聽到畢律斯因為學校要省電,要趕我們走,我就趕快–,幸虧沒被他抓到。不過抓到也無所謂啦。
創辦《東海文學》
許達然121
當時,同學對我都非常好,林清祥是我們那一屆的。我們那一屆現在在東海有三個﹕經濟系的
林清祥,政治系的蔡啟清,中文系的薛順雄。我們都處得很好。
莊紫蓉122
那時候您們會一起談文學嗎?
許達然122
沒有,有興趣的不多。不過我大四的時候,孫克寬老師希望我們辦個刊物。薛順雄(中文系)、張中芸(外文系)和我三個人辦《東海文學》,1961年,我大四的時候,是我編的,錢是我們三個人出的,我記得一期大概要一千塊,我們一個人出三百多。薛順雄編古詩,張中芸負責翻譯,我負責拉稿,拉不到就自己翻,我是打雜。那時候我還跟張秀亞、覃子豪拉稿,我不認識她,就寫信,戰戰兢兢寫信跟那些人拉稿。
莊紫蓉123
多久出一期?
許達然123
我現在忘了,32開很小一本。假如我沒記錯的話,好像是孫克寬希望有這樣一本刊物。因為那時候我有獎學金,有時候投稿,中央日報的稿費很高,所以有一些積蓄。
莊紫蓉124
這本刊物的內容是—
許達然124
希望能融合舊的跟新的。因為那時候的文藝刊物,不是舊的就是新的。《東海文學》有個特色,不管新舊都放在一起,舊的當然是詩跟詞,蕭繼宗老師也寫,孫先生也寫,還有陳問梅。陳問梅那時候在圖書館,他是中文古籍的編輯,還沒有在中文系教書。還有陳曉薔,她也寫詩或填詞。還有徐道麟,那時候是政治系的教授,他古文根底很好,偶爾也寫詞,他的稿子好像是我去跟他要的。還有顧敦鍒,那時候的文學院長。薛順雄偶爾也寫寫。
| 第24屆吳三連獎贈獎典禮 吳三連獎文學獎得主 許達然 2001年11月14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125
您也寫嗎 ?
許達然125
對,每一期都有。
莊紫蓉126
是在校內發行?
許達然126
對。你那時候有《東海文學》嗎?
莊紫蓉127
沒有,有《東風》。
許達然127
《東風》是一向就有。《東海文學》可能停了一段時期,然後文學院接辦。1983、84年我在台灣一年,84年我回東海給了兩、三個演講,有一個是文學院的演講,一個是社會所和歷史所合起來的,社會所跟歷史所要我講歷史社會學,文學院的好像是講文學社會學,那時候文學院長是江舉謙,他就給我一本《東海文學》。
莊紫蓉128
後來的《東海文學》就比較大本?
許達然128
那時候我看到的是16開的。現在我又聽說目前屬於中文系,我沒有看到,因為現在中文系除了洪銘水跟薛順雄以外,我跟其他人不熟。
莊紫蓉129
現在的《東海文學》和您以前辦的很不一樣囉?
許達然129
不一樣,不一樣。現在很少人肯出一點錢辦文學刊物,有沒有人讀都不管的那種傻勁。
莊紫蓉130
現在《台灣文藝》訂戶少,看得人也很少。
許達然130
《台灣文藝》現在是誰辦?
莊紫蓉131
台灣筆會。傅銀樵主編。鍾老還是念念不忘《台灣文藝》。
許達然131
他從一開始就—
莊紫蓉132
最近他把台視給他的《魯冰花》電視劇的版權費40萬捐給《台灣文藝》。
許達然132
對對。我6月回來東海講座時有看到鍾老捐錢的報導。坦白講,現在《台灣文藝》水準並不好哦?!
莊紫蓉133
沒有稿子啊。
許達然133
這也牽涉到台灣人的不團結,可以用大家的力量好好辦一個刊物啊。現在卻不是,各辦各的,一些小意見就鬧翻,我覺得很不好。
莊紫蓉134
沒辦法集中力量。好像我們現在還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可以有那麼多本刊物。
許達然134
就是啊。反正是虧本的東西,一起把它辦得很有水準,或者辦個學報,我的理想是辦個學報,這就講得比較遠了。我的理想一向是一個國際水準的學報,有關台灣研究的,包括文學、歷史,或其他。主要是用中文寫,用其他任何語言—日文、英文、法文等等—也都可以,變成一個國際的園地,用民間的力量。
莊紫蓉135
其實,您這樣的構想,台灣筆會可以做吧?
許達然135
現在會長是誰?
莊紫蓉136
李喬。
許達然136
哦!還有個益壯會,你參加嗎?
莊紫蓉137
沒有。
許達然137
我83、84那一年每次都參加,那時候最年輕的是我,第二年輕的恐怕是鍾老,哈哈,其他都是日治時期的台灣老作家。
文學創作的動力
莊紫蓉138
鍾老心裡有個作品要寫,就是以歌德的愛情與文學為本來寫。歌德好像年紀很大了還談戀愛。
許達然138
這我不知道。
莊紫蓉139
作家寫作會有個動力吧?
許達然139
我想應該有吧。
莊紫蓉140
好像很多作家寫作的動力是愛情。
許達然140
對,歌德也是,他很年輕的時候戀愛,在海德堡有個橋,我去過。但丁那個橋在佛羅倫斯,我也去過。他們那兩個橋,都跟戀愛有關係。
莊紫蓉141
鍾老說過他寫作的動力是使命感,您寫作的動力是什麼?
許達然141
真的沒有什麼動力欸,真的想不出有什麼動力。跟戀愛沒有關係,那是肯定的,因為只戀愛過一次,哈哈。真的沒有什麼,講得堂皇一點,勉勉強強說是使命感,除了堅持藝術性外,也要用良知和社會意識。戀愛的,恐怕是失戀才會成為動力,假如沒有失戀的話,我不知道會不會成為一個動力。
莊紫蓉142
您說失戀才會成為寫作的動力,那是不是說痛苦的感受是一種動力?
許達然142
也可能。
| 台中東海大學 許達然 2001年11月12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143
寫作好像是很個人的,每個人不大一樣。不過,是不是有一些共通的,比方說發自內心的、有什麼想要表達—
許達然143
什麼動力很難講,可能是一種衝動,可能還沒到動力的階段。
莊紫蓉144
讀者的反應會不會有影響?
許達然144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寫的東西可能很少人看,所以,反應除非寫成評論我可以看得到,其他我就不知道。基本上,主要是沒有什麼讀者,也沒有跟讀者有什麼交流,所以就不知道。
莊紫蓉145
沒有讀者的話,您還是會繼續寫?
許達然145
對,雖然很諷刺的,沙特講過,一個文學作品沒有人讀的話就不存在。可是沒辦法,只好寫。
莊紫蓉146
不過至少有自己一個讀者。
許達然146
對。近來我是有創作,可是已經有四、五年沒有發表了。
| 第24屆吳三連獎贈獎典禮 台北國賓飯店 莊紫蓉(左)、許達然(右) 2001年11月14日 圖片提供:莊紫蓉 |
 |
莊紫蓉147
為什麼沒有發表?
許達然147
事實上也不知道要寄到哪裡發表。《文學台灣》有一篇。笠詩刊,我也有五年沒有寫詩了。《聯合文學》,我是掛名編委之一,每一期都會寄給我,我也很久沒有寄稿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