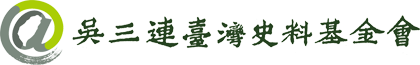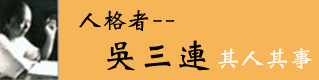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
一個隱性客家台美人的覺醒 陳憲治回憶錄 口述:陳憲治/整理撰寫:王倩慧 江昀 |
導讀
客家認同與臺灣認同的追尋:一位客家臺美人的素描
文/許維德(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初到美國的時候,不太會講客家話,在臺灣同鄉會裡都是講閩南話[1],……然而成立客家同鄉會之後,能和鄉親講客家話,則是很愉快的事。我不會忘記我的母語。
──陳憲治[2]
一、導言
這本傳記的主人翁陳憲治先生,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兩年的1943年出生於桃園平鎮(當時屬新竹州中壢郡平鎮庄),是家中年紀最小的孩子,上有五位兄姊。他的父母親都是來自平鎮的客家人,但兩家使用的客家話腔調並不相同:父親家是四縣腔,來自平鎮南勢的母親家則講饒平腔。憲治的老家雖然在桃園平鎮,但卻在小時候就舉家遷往臺北市昭安市場(1961年改名為中山市場)的後面。他從小就很獨立,學校成績也很不錯,先後畢業自日新國民學校、建國中學(初高中部)、臺大電機系,算是求學路上十分順利的好學生。
依循著當時臺灣社會「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時代風潮,大學畢業、服完兵役、並在母系任職助教一年的憲治,於1969年到位於美國德州拉伯克(Lubbock, Texas)的德州理工大學(Texas Tech University,1969年以前的名稱為Texas Technological College)電機研究所讀碩士,並於兩年後拿到碩士學位。1972年,在同校就讀的前妻也拿到物理學碩士後,他們搬遷到德州的最大城休士頓。憲治一方面於休斯科技公司擔任電機工程師,另一方面也開始在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的電機研究所繼續攻讀博士。1980年,憲治再一次搬家,從南部的德州搬到西岸的加州,於洛杉磯的軍火公司上班,也在因緣際會中開始參與該地的臺灣人活動,包括1985年與王秋森、陳婉真等人共同創辦《臺灣新社會》這份重要的臺美人刊物。
也是在這段時期,憲治碰到了重要的客家臺美人領袖楊貴運,共同在洛杉磯組成「臺灣客家同鄉會」這個組織。1988年,「全美臺灣客家會」於洛杉磯宣告成立;1991年,在客家大老鍾肇政的鼓勵下,「北美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也於洛杉磯宣告成立。恭逢其盛的憲治對這兩個組織均出錢出力、多所參與。
1990年,憲治於新一波的經濟衰退潮中被裁員,再加上已束縛臺美人多時的黑名單政策終告解除(他曾經因為被列入黑名單而無法在父親過世時回臺奔喪),他決定返臺貢獻所學。他先是在1990年至2000年的這十年間往返臺美兩地(因為當時尚未離婚的前妻不願意返臺),並在2000年之後完全在臺灣定居下來。在鮭魚返鄉後,憲治先後參與過「客家世界網」網站(http://www.hakkaworld.com.tw/)、「寶島客家廣播電臺」、「臺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臺灣客家文化數位發展協會」以及「臺灣客家山歌團」等客家相關的活動,直到今天。
在解讀歷史事件或理解傳主各種不同形態之認同的發展歷程上面,傳記的重要性不言可喻。[3]而在臺灣的出版市場中,傳記類圖書也一直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至少在絕對數量上就十分可觀。[4]那麼,這樣一本篇幅不算太多的傳記,相較於其他大量各種各樣的傳記,到底有著什麼樣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呢?
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分別從「臺美人研究」、「客家研究」,以及「客家臺美人研究」等三個視角,來論證這本傳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二、臺美人視角下的凝視
作為一位在大學畢業後就赴美求學就業、在美國奮鬥20餘年、並在1990年代以後又鮭魚返鄉的回臺人士,陳憲治這本傳記的第一個閱讀視角,顯然和所謂「臺美人」(Taiwanese American)──特別是第一代「臺美人」──的這個議題有關。[5]從這樣的凝視出發,筆者覺得這本傳記有以下幾點值得多加注意的地方。
首先,和很多臺美人一樣,傳主從臺灣到美國後的這個「美國經驗」,顯然對其政治認同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在來美國讀書以前,憲治雖然潛意識中似乎有某種模糊的臺灣意識,但卻一直要等到人到了美國以後,他在政治上才有所啟蒙,變成了海外臺灣民主運動的熱心支持者。
就赴美前的經驗而言,他提到了在建中讀書時老師們的「外省腔調」:「老師講話全都是外省腔調,特別是國文和公民老師的口音我幾乎都聽不懂,因此大學聯考時我國文才考50幾分,三民主義才30幾分」(頁105);以及國慶日時被學校要求要到總統府前集合等蔣介石出來揮手的經驗,「這讓我非常生氣,也非常討厭,真的是很辛苦,大家都會抱怨。……一點意義都沒有,真是浪費我們的生命」(頁107)。至於在臺大讀書的時候,憲治則是有注意到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個人於1964年因為〈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而被逮捕的事情(頁122);也有聆聽當時以無黨籍身分競選臺北市市長之高玉樹演講的經驗(頁123)。不過,總體來講,傳主數度用「寡言少語」(頁148)、「孤僻」(頁110)等語彙來描摩出國前的自己。換句話說,即使對當時的政治現狀有所不滿,傳主也並未萌生出任何站出來和這一政權進行抗爭的想法。
但是,在1969年到美國讀書以後,這位向來沉默的年輕人,卻因為美國自由環境的影響而成了一個「好插事」的熱心份子。他這樣描述這個美國經驗對自己的影響:
另外像是1958年金門發生的八二三砲戰,我也只知道兩邊打來打去,也沒有在發起或參與什麼聲援活動,在我當時接觸到的層面,都沒有這種有關政治的參與,我個人有政治思想的期望,或是說對政治運動的啟蒙,要到我出國留學以後才開始萌芽,出國是一個轉捩點,個性才變得比較「好插事」。(頁114;重點是加上的)
我的個性寡言少語,擁有自己思維的關鍵,則是在念大學到出國的這個階段,在美國的自由環境裡,我除了念書、工作之外,還參加了不少的活動,不會只執著在家庭和工作上。(頁148;重點是加上的)
第二,憲治並不僅僅是臺美人中一般的泛泛份子,他其實是一位參與頗深的海外民主運動熱心份子,特別是在1980年到洛杉磯的軍火公司上班以後。這本傳記這樣描述憲治在這段時期的活動:
在思念自己的故鄉,想多為臺灣盡一份心力的驅使下,1983年,我就和王秋森、陳婉真等臺灣同鄉,在洛杉磯成立了「臺灣文化事業公司」,想要建立本土性、進步性、草根性的臺灣文化,而在我當選「洛杉磯臺灣同鄉會」會長之時,再和同好創辦了《臺灣新社會》雜誌。(頁148-150)
事實上,洛杉磯或範圍更廣的南加州,一直都是臺美人在美國最重要的活動舞臺。一方面,在美國全境有將近四分之一的臺美人是居住在大洛杉磯地區(McCabe 2012),是美國最大的臺美人聚集地(Guerra 2015: iii)。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洛杉磯,由於大批投資移民在美麗島事件和臺美斷交後湧入此地,各種華文報業──比如說《世界日報》、《美洲中國時報》、《國際日報》、《臺灣日報》、《臺灣時報》和《太平洋時報》等──相繼在洛杉磯宣告成立,同時也將各種政治勢力導入此地,包括當時流亡南加州的前桃園縣縣長許信良。
憲治所參與的這本《臺灣新社會》雜誌,正必須放在上述脈絡下來理解。這本雜誌的創辦人是前臺大公衛學院院長王秋森教授。1982年,時任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6]化工系教授的王秋森,因為對許信良在美復刊之《美麗島週報》的支持,決定辭掉正教授職位,舉家西遷洛杉磯,全力投入臺灣人運動的行列(許維德 2001:118)。1985年7月,《臺灣新社會》這本印刷、內容均十分具專業水準的月刊開始出刊,一直到1988年9月第39期為止,總共運作了將近3年多(許維德 2001:118)。[7]
另外一件值得注意、但是在這本傳記卻未提到的事情,在於憲治在參與臺美人相關事務時所使用的「假名」。在關於「臺灣文化事業公司」和《臺灣新社會》的一些既有史料(特別是與王秋森有關者)中,多半會有以下類似的敘述:「[王秋森]與陳婉真、陳進財、李賢群成立『臺灣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臺灣相關書籍並發行《臺灣新社會》月刊」(財團法人四二四教育基金會籌備處 2020)。[8]事實上,這裡的這位「陳進財」,正是我們的主角憲治。憲治之所以要使用「進財」這個假名,顯然和當時國民黨的黑名單政策有密切的關係。
最後一點,憲治在1990年代以後鮭魚返鄉的這個抉擇,其實也是不少臺美人的縮影。比如說,在我博士論文所描述的6個臺美人個案研究中,其中就至少有一半的個案(彭明敏、蔡同榮、陳芳明)在後解嚴時期回到了臺灣,結束其旅美生涯(Shu 2005: Ch. 5, Ch. 7, and Ch. 9)。嚴格來講,對這些已經在美國居住了20年、甚至更久時間的臺美人而言,這個回臺的決定並不容易,特別是如果我們考量到其家庭成員的話。憲治這本傳記值得一讀的地方之一,就在於他明確指出了這一抉擇的艱難,甚至還因此和前妻離婚:
她[前妻]無法瞭解和體諒我的思鄉情懷,我也無法繼續漂泊在不屬於我的國家中生活,彼此意見不合,我們選擇了互相祝福,在屬於自己天空下繼續努力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頁145:重點是加上的)
在這本傳記中,這類描述雖然不算多(畢竟涉及太多隱私),不過,卻是這些離鄉背井卻又日夜思念故鄉之臺美人的絕佳寫照。
三、客家研究取徑的閱讀
除了「臺美人」這一視角,這本傳記的另一個亮點,就在於傳主的「客家人」身分。從「客家研究」的角度來看,雖然我們目前已經累積了不少客籍人士的傳記,[9]但由於這本傳記相對於其他「名人」傳記的「常民性」,依舊有不少特別的素材可以和客家研究的某些重要發問進行對話。憲治在這本傳記中花了不少篇幅談他自己的客家經驗,包括小時候被鄰居和國校同學欺負的事例:
小時候的鄰居和學校周遭多是閩南人和外省人,接觸的人也多是講華語或閩南語,但是我和閩南人、外省人沒什麼交集,他們知道我是客家人就歧視我,雖然會一起走路去上學,但不會理我,和同學一起玩官兵捉強盜遊戲時,我只能被派去當小兵小卒,這些都讓我感到自卑,深深感受到作為一個客家人的悲哀。小學五、六年級的同學都會用「客人仔、客人仔」叫我,這就是很明顯的例子,我就會覺得說,我是客家人,和別人又有什麼不一樣,為什麼要打壓我,為什麼待遇會有不同,會這樣去思考,那時候就已經產生了一種所謂的客家意識。(頁91-2;重點是加上的)
事實上,憲治的「客家意識」並不僅會以上述「負面表述」的方式現身,也會以「找尋客家人」的方式出現在生命史的不同階段。在中學時期,後來當上醫生的古姓友人,是他中學6年最好的朋友:「中學六年裡面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這位古醫師,我們一直是建中同學,有一次還被分配在同一班,後來我們也都去到美國,在美國也常見面」(頁101)。而這位古醫師,碰巧也是苗栗的客家人。
至於在大學時期,在舞會等男女兩性得以有接觸機會的場合,憲治只要一有機會和女生互動,念茲在茲的,竟然還是她是否為客家人:
遇到女生,我第一句話就會問:「妳是哪裡人?」如果是客家人,我就會跟她聊比較久,客家意識就這樣慢慢的顯現出來。我問過一個外文系的,問她是哪裡人?她說是竹東人,我再問她會不會講客家話,她說會啊,再問是四縣還是海陸,她說是四縣,所以整個晚上大部份的時間就一直跟她聊天。(頁121;重點是加上的)
我聽一下對方的口音,大致就可以判斷是不是客家人,在派對上很容易做到。我喜歡跟客家人做朋友,問到對方也是客家人,我就會很高興,就會聊多一點,如果不是客家鄉親,就會想說應付應付就好,潛意識中就是在尋找客家的女孩子,就是要跟客家連接在一起,這某種程度是故意的、傳統的,想跟客家人在一起,想找一個客家人的女朋友,尤其是跟她講客家話,講四縣腔我就會感到更加親切,海陸我還不太會講。(頁121;重點是加上的)
雖然有著上述那種近乎「原生」的客家情懷,但憲治卻也提到,至少在臺灣的脈絡下,嚴格意義下之「客家運動/意識」的誕生,其實是要到後解嚴時期才真正開始的。他這樣表示:
臺灣的客家運動,一直到解嚴後才真正開始。1990年12月,「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以下簡稱客協)成立,創會理事長鍾肇政在協會成立宣言中,提出「新个客家人」的口號……鍾肇政希望能喚起客家人的族群自覺,並推動民族參與,我認為從這時開始,才是臺灣客家意識興起的開始。(頁182-4;重點是加上的)
事實上,由於離開臺灣前的那段時期受到華語霸權的壓迫,到美國讀書以後又處於臺灣同鄉會主導的福佬/福老話霸權之下,再加上前妻也不是客家人,小時候客語十分流利的憲治也坦承表示,他的母語能力似乎逐漸喪失,[10]是後來鮭魚返鄉之後的這段時間才又慢慢「找回來」的。他如此描述自己參與客家廣播電臺的經驗:
我每次準備這個節目就要花掉半天的時間,剛回來臺灣時客語沒有很流利,也是要花時間準備的原因之一。為了主持節目讓我重新認真學習客語,逼著我慢慢的把母語找回來。(頁193;重點是加上的)
那麼,從「客家研究」的角度出發,憲治上述的客家經驗,到底對我們有著什麼樣的啟示和洞見呢?筆者曾經寫過一篇以「臺灣客家認同之出現時間」為主要發問的論文,藉以和客家研究中「客家『族群想像』新生現象說 vs. 『客家』持續說」這兩種不同的論點進行對話(許維德 2013c)。前者這種觀點認為,做為一種現代性的「族群想像」,當代臺灣的「客家」認同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才出現的新生現象,必須被放在崛起於後解嚴時期之客家社會文化運動的這個脈絡下來理解(e.g., 王甫昌 2003)。後者這種觀點則認為,「客家」這個集合體概念早在100年前、甚至更久以前就已經存在,因此,在臺灣的脈絡下,某種意義的「客家認同」也就一直存在於講客語的這群人當中,只是早期並未使用「族群」或者是「認同」的概念來描述這個實存的現象(e.g., 羅烈師 2006)。為了解決這一涉及「客家認同出現時間」的重大爭議,筆者遂在上述研究中以8位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的生命史為主要素材,探究其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客家認同」內涵,藉以回答「大社會」在不同時間點的「客家認同」性質。
該研究有幾個重要發現。首先,和所謂「『客家』持續說」的論點相符,多數個案在其生命史前期,的確存在著某種以「文化」為核心要素的「客家認同」,筆者將之稱為「素樸文化認同性質的客家認同」。第二,和「客家『族群想像』新生現象說」的看法相符,多數個案在生命史後期之「客家認同」,的確呈現出某種程度的「質變」,主要是和「政治」或「社會」領域相關的一些制度性安排息息相關的,筆者將之稱為「制度化政治認同性質的客家認同」。第三,綜合上述兩點的發現,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將戰後臺灣「客家認同」的發展簡單描述為「從『素樸文化認同』到『制度化政治認同』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有其「連續性」,另一方面也有其「變化性」(許維德 2013c)。
抱持著上述視角來閱讀憲治的生命史,筆者覺得,這樣的生命故事,其實和筆者的研究發現有相當程度的契合。一方面,傳主自己也承認,「從[『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的1990年]這時開始,才是臺灣客家意識興起的開始」(頁184),從而彰顯出「客家『族群想像』新生現象說」的論點。但另一方面,傳主童年時被喊成「客人仔、客人仔」的受歧視經驗、乃至中學和大學時「找尋客家人」的經驗,卻也都告訴了我們,解嚴前和「客家」(雖然在民間社會層次是以「客人」來稱呼)這一人群分類標籤相關的現象,並不見得是不存在的。在這樣的視角下,「『客家』持續說」的論點,也不能說完全不成立。總結來講,筆者自己「從『素樸文化認同』到『制度化政治認同』」的這個詮釋,似乎也頗能在這本傳記中得到印證。
四、結合臺美人視角與客家研究取徑的客家臺美人傳記
除了上述「臺美人」和「客家研究」這兩個視角,這本傳記最特別的地方,莫過於這兩個視角的結合,而創造出「客家臺美人」傳記這樣的「新(?)」文類。當然,在美國的臺美人社群中,本來就有相當比例的人具備客家身分,當中也有少數幾個人出版過相關的傳記性書籍,比如說上述曾經在美國流亡了10年左右的許信良(e.g., 許信良、鍾碧霞 1992;夏珍 1999;林哲藝 2004);來自楊梅的前輩作家黃娟(e.g., 張恆豪 2018;王倩慧 2019);以及出身苗栗三義,原本是美國德州某公部門工程師,後來自行創業做進口傢俱批發生意的企業家陳國洸(e.g., 陳國洸 2003[11])等。不過,這類傳記一方面在數量上實在太少,[12]另一方面在內容上「客家」也幾乎都不是書寫重點,要將之稱為「客家臺美人傳記」(雖然傳主在客觀上具備這樣的身分),恐怕是有一些概念上的困難。
但憲治這本傳記,卻紮紮實實地提供了不少真的和「客家臺美人」相關的訊息。首先,當傳主人還在美國洛杉磯的時候,就陸續參與過不少客家臺美人社團的創立活動,比如說「臺灣客家同鄉會」、「全美臺灣客家會」、以及「北美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等。憲治這樣描述他與臺美客家大老楊貴運的邂逅、以及共同在洛杉磯成立「臺灣客家同鄉會」的過程:
我住在洛杉磯的時候,有一天在公園遇到了一位臺灣鄉親楊貴運先生,我和他談了一會兒,聽他的腔調很像是客家人,一問之下,知道他是楊梅人,是一位化工博士;於是我們常相約見面,開始談論在洛杉磯建立一個客家同鄉會;我們一致的認知是:「閩南人可以成立『臺灣同鄉會』,為什麼我們客家人不能成立『客家同鄉會』?」
楊貴運贊成我的想法,於是我們兩個就講好,下一次的聚會希望各帶幾位客家朋友一起來參加。我們分頭去找認識的客家人,大概是十來戶,然後固定時間聚會,漸漸形成一個「臺灣客家同鄉會」這樣的組織。(頁150-1;重點是加上的)
有了上述基礎,規模更大、涵蓋全美各地的「全美臺灣客家會」,也於1988年在洛杉磯宣告成立:
到1980年代,臺灣客家同鄉會仍屬於聯誼性質,1988年才在洛杉磯組成整合全美臺灣客家社團的「全美臺灣客家會」,而我們都是利用業餘時間參加客家同鄉會的聚會,活動就以聯誼的宗旨來規劃,成員數自然擴大,並沒有想過往後如何發展的問題……。(頁159)
憲治也見證並參與了1991年「北美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的成立,已如上述。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客家臺美人」社團,基本上都和臺美人所成立之「臺灣同鄉會」等組織有一定程度的互動或互補關係。根據憲治的描述,基本上,「臺灣同鄉會」政治性比較強,「臺灣客家同鄉會」則比較去政治,是以日常生活的關懷為主軸。但是,時間久了,透過憲治等「有心人」的中介,這兩者之間也會有一定程度的互動和交流:
最初,臺灣客家同鄉會談的是客家鄉親的生活,並不關心其他敏感問題,不像「臺灣同鄉會」偏重關心臺灣社會發生的事件,有沒有人被抓去?臺灣客家同鄉會不談政治,就是與臺灣同鄉會最大的分別。但後來我會慢慢帶動客家鄉親開始關心時事,在臺灣客家同鄉會裡,因為大家都不談政治,我也不談,可是有的時候我會告訴他們一些我知道的事情,有的人會聽進去,認識久了,我就知道他可能會比較關心政治,就會帶他去參加臺灣同鄉會。所以有一些客家人跟我一樣,同時跨足「臺灣同鄉會」和「客家同鄉會」。(頁152-3;重點是加上的)
第三,所謂的「客家臺美人」還有一個重要的意涵,那就是「客家」是「臺美人/臺灣人」的一個子集合,因此是所謂的「臺派」,基本上是反國民黨的。憲治這樣描述那些「非臺派」之客家組織的情況:
國民黨無法坐視臺灣同鄉會的組織越來越強大,於是就成立「臺灣同鄉聯誼會」來打對臺,住在美國的客家人人數比較少,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活動,因此,就沒有像臺灣同鄉聯誼會一樣性質的團體出現,正宗的臺灣客家同鄉會的名稱,大多就是在臺灣客家同鄉會之前掛上當地地名,像是「洛杉磯臺灣客家同鄉會」,如果立場不同,較後期才成立的,名稱的變化就非常多,像是會加上一個「文化」之類的字樣,反正和正宗的臺灣客家同鄉會不一樣,在紐約就有一個「紐約臺灣客家同鄉會」,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很「有心」,會刻意找一些立場偏國民黨的客家人加入,我們一看誰做會長,就知道他的立場。(頁159-60;重點是加上的)
最後,憲治在美國的時候,參與的是所謂「臺美人」(比如說上述「臺灣文化事業公司」和《臺灣新社會》雜誌)或「客家臺美人」的相關活動。至於回臺灣以後,雖說對臺灣的關懷不曾減低(不然就不會做出鮭魚返鄉的抉擇了),但其活躍的舞臺,卻似乎都有「客家」的身影。換句話說,「客家臺美人」的這個身分,在某種意義上質變為「客家臺灣人」的身分,在各種各樣的「客家舞臺」上發光發熱,包括「客家世界網」網站、「寶島客家廣播電臺」、「臺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臺灣客家文化數位發展協會」、以及「臺灣客家山歌團」等客家相關的活動。他自己這樣說道:
回來臺灣,我更積極的參與客家活動,比如說幫助客委會籌備「客家網路學苑」,也會像鍾肇政先生對我們做的一樣,去鼓勵其他人成立協會。我現在的太太(陳淑姬)去淡水教客家歌謠,我也跟著去。我碰到住淡水的客家人,他們沒有組織團體。我就找一兩個比較熱心的朋友,遊說他們籌組一個協會,理所當然的由我擔任他們的顧問,教他們填表、申請,現在「淡水客家文化協會」就是新北市最大、最多成員的文化協會。(頁161-2)
他因此這樣總結自己的「客家」活動參與:
有時想想,我這一生中,在大學裡學得的專長,真的像是用來混飯吃的,在美國,除了工作以外的時間,我都在參加各項活動;有些人,他們一生就在專業上奮鬥,我則是在為我的理想奮鬥,做一個真正的客家人。(頁162;重點是加上的)
五、代結語:斷層、時代印記與續集
總而言之,這是一本從不同視角都可以得到某些閱讀樂趣的傳記。除了上述「臺美人」、「客家研究」,以及「客家臺美人」的角度,在結語這節,筆者也想從幾個和「族群研究」比較無關的地方著手,再指出本書其他一些值得再提出討論的議題。
首先是「斷層」這一主題。傳主在本書不同的地方,一再地使用「斷層」這個字眼來描摹自己的生命:
時代的斷層對一個人影響很大,在我的生命中就有三個斷層,第一個是我們家的鄰居通通都是閩南人,我被歧視,沒有知心好友;第二是父親兄姐受日本教育,我卻受國民教育,沒有人可以教我;第三、我去到美國參加「臺灣同鄉會」裡面都是閩南人,我又是語言不通的一個,一生有過三個斷層的人,想必不多,我算是奇蹟了吧。(頁110;重點是加上的)
我們先看上述第二個斷層。傳主出生於二戰末期(1943年)的這個背景,就注定會是一個所謂「斷層」時代的孩子,因為父母親和五個兄姊都是受日本教育、在日治時期成長的世代,但憲治卻是受華語文教育的戰後世代,彼此間甚至連語言都不通,「平常家人講話,是客語和日語交互使用,日語我聽得懂,但是不會講」(頁88),而「[憲治]接受的是華語文教育,兄姊對我所學的課程,完全無法理解,沒有人能教我」(頁88)。
至於上述引文的第一個和第三個斷層,倒是都和「客家 vs. 福佬/福老」的這組對立有關。小時候住在多數人都是福佬/福老人的環境,想必對憲治小小的心靈,有著不小的影響:「小時候因為鄰居──甚至整個社會環境周遭[──]都是閩南人,沒有辦法改變,只好接受成為隱性客家人」(頁182)。而到美國讀書之後,又碰到了類似的情境,必須面對講著福佬/福老語的臺灣同鄉會夥伴:「初到美國的時候,不太會講客家話,在臺灣同鄉會裡都是講閩南話,我當時的太太也是閩南人,所以在美國的時候,我的閩南話講得比客家話好,起初有一些失落感」(頁158)。
第二,這本傳記,其實也留下很多「時代的印記」。從筆者的角度來看(傳主和筆者差了20餘歲,約略是筆者的父親輩),本書的很多敘述都已經不是我所親身經歷過的事物,而是在時代巨輪推移下逐漸消逝的往事。比如說,憲治小時候在中央戲院看日本武打片的經驗(頁92-3),基本上是他那個時代的故事;雖然小時候筆者的阿公也常帶我到中央戲院附近閒逛,但因為後來日本電影被全面禁止在戲院播放,[13]我完全沒有在電影院看日本武士電影的經驗。再比如說,回到平鎮外婆家的憲治,竟然還有在陂塘釣魚(頁94)、在小溪裡用泥巴堵水捉魚(頁95)、甚至是看見殺豬(頁95)的經驗,那就已經是我完全無法想像的事情了。至於大學時所流行的所謂「阿哥哥」舞(頁119),更是我只在電影中看過的場景。
不過,這本傳記還是有些描述,因為和我自己小時候的經驗相符(雖然現在已不復見),讀來就頗有會心一笑的效果。比如說,坐公車時車上有車掌小姐,也還有厚紙做的月票:「記得當時是搭14路公車,車上還有車掌小姐,從後門上車前門下車,我們學生都買月票,車掌小姐就會在車票上剪一個洞」(頁102)。再比如說,中學讀書時參與救國團的活動到中橫健行(頁103-4),也是筆者那個年紀時的重要經驗,一直到現在都還有印象。
筆者對這本傳記的最後一個感想是讀不過癮。基本上,我覺得這本傳記在篇幅和字數上都過於短小了,很多事物雖然有提到,但是都敘說得過於簡潔,頗讓人有意猶未盡的感覺。筆者誠摯希望,這本傳記的出版,只是一個開端而已,傳主應該要嚴肅考慮再出第二本傳記的可能性。畢竟,這是第一本相對嚴格意義下的「客家臺美人」傳記,值得寫,也應該要再寫。
參考文獻
王甫昌,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
王秋森,2016,〈憶許永華兄〉。《臺美人歷史協會》,5月30日。https://www.tahistory.org/憶許永華兄-◎-王秋森,取用日期:2020年11月15日。
王秋森等,2017,《一九四七臺灣二二八革命》,三版。彰化縣田中鎮:陳婉真。
王倩慧,2019,《活出愛:黃娟傳》。桃園市: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臺美史料中心,2015,〈臺灣新社會〉。《臺美史料中心》,10月10日。http://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the-taiwanese-new-society/,取用日期:2020年11月15日。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2005,《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4年度》。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___編,2006,《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5年度》。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___編,2007,《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6年度》。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___編,2008,《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7年度》。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何明修,2008,《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臺北:群學。
吳木盛,2000,《鴉勇的腳印:我的回憶》。臺北:前衛。
吳嘉陵、吳嘉梓,2008,《走過時代的典範:客家私塾老師林漢唐之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余玲雅等計畫主持,2005,《吳伯雄先生訪談錄》。臺中縣霧峰鄉:臺灣省諮議會。
李正三,2009,《七十回顧:輕舟已過萬重山》。臺北:草根出版事業。
李俊達等編,2017,《賭鬼的後代:魏廷朝回憶錄》。臺北:前衛。
李勤岸,2007,〈找回我們的名字〉。《臺灣文學館通訊》15:37-41。
李靜宜,2003,《臺灣傳記圖書類型及其發展》。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建中,2007,《林建中八秩回憶錄:臺灣民主運動與宗教信仰告白》。臺北縣中和市:新文京。
林哲藝計畫主持、臺灣省諮議會編,2004,《許信良先生訪談錄》。臺中縣霧峰鄉:臺灣省諮議會。
林瑛琪,2009,《鄧雨賢》,再版。臺中市:莎士比亞文化。
林靜竹,2006,《臺美生涯七十年》。臺北:前衛。
邱垂亮,2013,《有緣相隨:我的「非回憶錄」》。臺北:玉山社。
施添福,2014,〈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3:1-110。
徐亞湘,2011,《母女同行:阿玉旦‧黃秀滿的客家戲曲人生》。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
______,2012,《老爺弟子:張文聰的客家演藝生涯》。宜蘭縣五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夏珍,1999,《許信良的政治世界》,新版。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根雨屋,2019,〈當年要看日本電影?很抱歉不行〉。《芋傳媒》,5月17日。https://taronews.tw/2019/05/17/340316/,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1日。
財團法人四二四教育基金會籌備處,2020,〈雪城的送暖者:王秋森〉。《財團法人四二四教育基金會籌備處》,7月21日。https://424.org.tw/character-story-1-7/,取用日期:2020年10月29日。
商周編輯委員會編著,2009,《感恩的心:吳伯雄七十留影》。臺北:商周出版。
張文隆編著、王能祥策劃,2013,《臺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新北市:遠景。
張恆豪編選,2011,《吳濁流:一九〇〇-一九七六》。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______編選,2018,《黃娟:一九三四-》。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張瑞芬編選,2011,《林海音:一九一八-二〇〇一》。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莫渝編選,2015,《詹冰:一九二一-二〇〇四》。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許永華,2009,《從美國看臺灣:人在美國,心想臺灣》。臺北:前衛。
許信良、鍾碧霞著、陳芳明編,1992,《許信良言論選輯:附〈隨夫波折十八載〉》。Irvine,Calif.:臺灣出版社。
許俊雅編選,2011,《呂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一》。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許維德,2001,〈發自異域的另類聲響:戰後海外臺獨運動相關刊物初探〉。《臺灣史料研究》17:99-155。
______,2013a,〈先成為人,再成為臺灣人〉。頁146-75,收錄於史明口述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第三冊)陸上行舟:1975-2010》。臺北:行人文化。
______,2013b,〈「社會建構論」的基本結構分析:以「族群是社會建構的」這一陳述為討論核心〉。頁111-50,收錄於《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臺灣客家、原住民與臺美人的研究》。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遠流出版社。
______,2013c,〈從「素樸文化認同」到「制度化政治認同」〉。頁223-64,收錄於《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臺灣客家、原住民與臺美人的研究》。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遠流出版社。
陳庚金口述、黃貴造等文字整理,2008,《耕餘園:陳庚金七秩紀實》。臺北:五南。
陳怡君,2007,《山歌好韻滋味長:賴碧霞與她的客家民歌天地》。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
陳建忠編選,2011,《賴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 》。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陳郁秀、孫芝君,2005,《呂泉生的音樂人生》。臺北:遠流。
陳國洸,2003,《臺灣情‧漂泊心》。臺北:前衛。
陳萬益編選,2011,《龍瑛宗:一九一一-一九九九》。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彭明敏,1984,《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Irvine,Calif.:臺灣出版社。
彭瑞金編選,2011,《鍾肇政:一九二五-》。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______編選,2012,《李喬:一九三四-》。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黃榮洛口述、彭瑞金訪問撰述,2015,《黃榮洛生命史:三十年臺灣文史路》。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
黃頤銘著、黃意雯譯,2015,《菜鳥新移民:臺裔刈包小子嘻哈奮鬥記》。新北市:木馬文化。
楊鏡汀口述、彭瑞金訪問撰述,2015,《楊鏡汀生命史:從大山背到內大坪》。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
廖述宗口述、莊家穎整理編寫,2012,《食果籽 拜樹頭:廖述宗的人生回憶》。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廖雪芳,2002,《醫者之路:臺灣肝炎鼻祖宋瑞樓傳》。臺北:天下雜誌。
劉美蓮,2016,《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新北市:INK印刻文學。
劉維瑛編選,2016,《杜潘芳格:一九二七-》。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蔡石山著、曾士榮、陳進盛譯,2007,《李登輝與臺灣國家認同》。臺北:前衛。
蔡同榮,1990,《我要回去》。高雄市:敦理出版社。
蔡明雲,2006,《世界級的臺灣音樂家:蕭泰然》。臺北:玉山社。
應鳳凰編選,2011,《鍾理和:一九一五-一九六〇》。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______編選,2016,《 鍾鐵民:一九四一-二〇一一》。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戴國煇,2002,《戴國煇這個人:含生平事記與著作目錄》。臺北:遠流。
羅烈師,2006,《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erra, Ferdinando et al.,2015,〈臺灣與洛杉磯郡〉。《Los Angeles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2月。https://laedc.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Taiwan-and-LA-Report-TRANSLATED-TRAD-CHIN_-FINAL-WEB.pdf,取用日期:2019年9月4日。
Hopgood, Mei-ling, 2009, Lucky Girl.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______(梅齡‧霍普古德)著、葉佳怡譯,2012,《被抱走的女兒:一個西方女孩回臺灣尋親的真實故事》。臺北:寶瓶文化。
Huang, Eddie, 2013, Fresh off the Boat: A Memoir.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Huang, Marijane, 2017, Beyond Two Worlds: A Taiwanese-American Adoptee’s Memoir & Search for Identity. Bloomington, Ind.: AuthorHouse.
Kagan, Richard C.(柯義耕)著、蕭寶森譯,2008,《臺灣政治家:李登輝》。臺北:前衛。
McCabe, Kristen, 2012,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31 January.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USFocus/print.cfm?ID=879 (Date visited: February 22, 2012).
Shu, Wei-der, 2005, Transform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Diaspora: An Identity Formation Approach to Biographies of Activists Affiliated with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yracuse University.
Stanford Libraries, nd, “Taiwan xin she hui = The Taiwanese New Society.” In Stanford Libraries.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4204315 (Date visited: November 21, 2020).
註釋
[1]. 「閩南語」(這是我的母語)是傳主在這本書中所使用的語彙。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用法筆者並不盡然同意。根據李勤岸(2007:39)的說法,就語言而言,上述被稱為「閩南語」的這個語言,存在著至少17個不同的名字,約略可以分成三大類:「臺語類」、「閩南語類」、以及「河洛、福佬或福老等類」。李勤岸(2007:40)整理了反對第二類「閩南語類」(包括閩南語、臺灣閩南語、以及福建話等具體用法)之用法的三種理由,包括「一、臺灣不是中國的閩南地區,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二、這個語言與中國福建的閩南語已經有很多不同,不能就叫做閩南語。三、閩南語本身有歧視性的意涵,『閩』就是『蠻』,是門內的蟲」。原則上這三個理由都能夠說服筆者。也因此,在筆者過去的專書中,我就選擇採用「福佬語」這個語彙來指涉這個語言(見許維德 2013c:232,234,238,242;關於這一選擇的主要理由,另見許維德 2013b:131,註52)。晚近另有研究者提出應該以「福老語」這一語彙來稱呼這一語言(e.g., 施添福 2014:7,13,23)。筆者對於到底該使用什麼樣的確切詞彙來指涉這一語言,尚未有清楚的定見。不過,我不會用「閩南語」這個語彙來稱呼這個語言,這倒是確定的事。以下這一語言出現在內文時,如果是引自其他人的引文,筆者原則上會遵循原作者的用法;但如果不是其他人的引文,筆者就會使用「福佬/福老語」這樣的標籤。根據張維安教授的說法,一般說來,口語上客家人並不會使用閩南人或閩南話,習慣上說是福佬人或福佬話,不過奇怪的是在寫作的時候經常是寫閩南人、閩南語(個人通訊 2020年11月22日)。
[2]. 見本書頁158。
[3]. 關於社會科學研究採用傳記材料來進行研究的簡史,可以參考Shu(2005: 116-121);關於傳記研究法既有的一些優點,也可以參考Shu(2005: 122-125);關於傳記材料在解讀傳主之政治價值與國族認同形成上的具體功用,如果以史明這位臺獨運動大老為例,則可以參考筆者之前為《史明口述史》這本書所寫的導讀文章(見許維德 2013a:154-156)。
[4]. 根據李靜宜(2003)的碩士論文,在1945年到2002年之間,臺灣總共出版了6,107本和傳記有關的圖書,約占所有圖書出版品的1.09%。筆者未找到時間更近之臺灣已出版傳記的數量。不過,如果以臺灣史這一領域為例,根據中研院臺史所從2005年就開始出版之《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的彙整(只有在前四年度單獨將「人物傳記」資料當成獨立類別,之後就會將這類資料放在其他類別中),這一領域在2004年至2007年所出版的傳記資料,每年也幾乎都在50筆以上(不限於圖書資料,見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 2005,2006,2007,2008)。
[5]. 和臺美人相關的各種傳記,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數目,雖然還少有人以這些材料來進行學術研究。在筆者於2005年完成之以美國臺獨運動參與者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Shu 2005)中,我找到了和22個參與者有關的傳記資料(僅限於書籍規模的資料,比如說彭明敏(1984)的《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蔡同榮(1990)的《我要回去》、以及吳木盛(2000)的《鴉勇的腳印:我的回憶》等),這些人多數也都可以被理解為「臺美人」。
在2005年之後,陸陸續續還有不下數十本臺美人傳記的出版,其中比較值得一提的包括:從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終身榮譽教授退休之林靜竹醫師(2006)所寫的《臺美生涯七十年》;蔡明雲(2006)為旅美音樂家蕭泰然所寫的《世界級的臺灣音樂家:蕭泰然》;留德博士,曾任臺大化工系系主任,在50歲過後才移民美國之林建中教授(2007)所寫的《林建中八秩回憶錄:臺灣民主運動與宗教信仰告白》;具企業家身分,但本人也從事過口述歷史工作之李正三(2009)所寫的《七十回顧:輕舟已過萬重山》;曾任世界臺灣同鄉會秘書長之許永華會計師(2009)所寫的《從美國看臺灣:人在美國,心想臺灣》(本書的前三分之一為作者自傳);中研院院士、芝加哥大學生化系退休教授廖述宗(2012)口述的《食果籽 拜樹頭:廖述宗的人生回憶》;以及張文隆(2013)為晚年在美國成立「臺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之臺灣民主運動前輩郭雨新所寫的《臺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等。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在身分上屬於第一代臺美人的傳主,在2005年之後,也有好幾本在身分上屬於第二代臺美人之傳主的傳記問世,比如說在臺東出生,但從小就被密西根白人夫婦收養之美國獲獎記者Mei-ling Hopgood(2009)所寫的Lucky Girl(本書有中譯版,見Hopgood(2012));具備第二代移民身分,在紐約市開人氣餐館賣刈包之Eddie Huang(黃頤銘)(2013)所寫的Fresh off the Boat: A Memoir(本書有中譯版,見黃頤銘(2015));以及出生在臺北,但也是從小就被美國家庭收養,現在南加州擔任社工員之Marijane Huang(2017)所寫的Beyond Two Worlds: A Taiwanese-American Adoptee’s Memoir & Search for Identity等。
[6]. 雪城大學剛好也是筆者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的母校。
[7]. 關於《臺灣新社會》最後一期的出刊日,這裡根據的是筆者之前關於海外臺獨運動刊物之梗概的田野調查報告(許維德 2001:118)。不過,我在網上又找到兩筆新資料,都顯示這一期刊的最後一期並非第39期,而是1989年8月出版的第40期(臺美史料中心 2015;Stanford Libraries nd)。如果這兩筆資料是可信的(應該沒有問題),這表示這一刊物在第39期(1988年9月)出版後,在11個月後又出版了第40期。至於這一刊物為什麼會在穩定出刊39期之後,中間停了11個月,然後又出刊了一期?由於我手上沒有第40期的刊物,暫時可能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8]. 類似的敘述,也可見諸於王秋森(2016)、王秋森等(2017:作者介紹)。
[9]. 在2000年以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至少數十本廣義之「客家人」傳記的出版。這些傳記的傳主多半是某種意義下的「名人」,比如說具備「文學家」或「音樂家」身分的文化工作者、包括學者在內教育工作者、以及廣義的政治工作者等。首先是「文學家」。如果以國立臺灣文學館自2011年所開始出版之「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這套書為例,我們可以看到賴和(陳建忠 2011)、吳濁流(張恆豪 2011)、龍瑛宗(陳萬益 2011)、呂赫若(許俊雅 2011)、鍾理和(應鳳凰 2011)、林海音(張瑞芬 2011)、鍾肇政(彭瑞金 2011)、李喬(彭瑞金 2012)、詹冰(莫渝 2015)、杜潘芳格(劉維瑛 2016)、鍾鐵民(應鳳凰 2016),以及黃娟(張恆豪 2018)等12位客籍作者的現身。這套書並非純粹的傳記,還會附上和該作家相關的二手研究文獻,不過,至少在形式上會包括一個名稱為「小傳」的文類。再來是「音樂家」,包括著名的流行音樂創作人鄧雨賢(e.g., 林瑛琪 2009);遊走於臺灣、日本、和中國三地的古典音樂大師江文也(e.g., 劉美蓮 2016);以本土為根、也採集、改編眾多臺灣民謠的音樂創作人呂泉生(e.g., 陳郁秀、孫芝君 2005);著名客家民歌演唱者賴碧霞(e.g., 陳怡君 2007);以及傳統客家戲劇傳人張文聰(e.g., 徐亞湘 2012)和黃莊玉妹、黃秀滿這對母女檔(e.g., 徐亞湘 2011)等。第三是學術和教育工作者,包括生於清領時期的客家私塾老師林漢唐(e.g., 吳嘉陵、吳嘉梓 2008);中研院院士、被譽為「臺灣肝炎之父」的宋瑞樓教授(e.g., 廖雪芳 2002);旅居澳洲的政治學者邱垂亮教授(e.g., 邱垂亮 2013);旅居日本的歷史學者戴國煇教授(e.g., 戴國煇 2002);以及鑽研客家文史的民間學者楊鏡汀校長(e.g., 楊鏡汀 2015)和黃榮洛(e.g., 黃榮洛 2015)。最後是政治工作者,包括前總統李登輝(e.g., 蔡石山 2007;Kagan 2008);前民進黨黨主席許信良(e.g., 林哲藝 2004);與彭明敏共同參與1964年〈臺灣自救運動宣言〉的魏廷朝(e.g., 李俊達等 2017);發動臺灣公路客運業界第一次的罷工抗爭的工運人士曾茂興(e.g., 何明修 2008);前國民黨黨主席吳伯雄(e.g., 余玲雅等 2005;商周編輯委員會 2009);以及前國民黨中評會主席團主席陳庚金(e.g., 陳庚金 2008)等。
[10]. 憲治自己這樣寫道:「初到美國的時候,不太會講客家話,在臺灣同鄉會裡都是講閩南話,我當時的太太也是閩南人,所以在美國的時候,我的閩南話講得比客家話好」(頁158;重點是加上的)。
[11]. 這本書並非嚴格意義下的自傳或傳記,而是一本收錄了近70篇散文的隨筆集。不過,因為很多內容涉及作者自己的生命故事(特別是母親和妻子),我們也可以用比較寬鬆的視角將這本書理解為某種意義下的生命書寫。
[12]. 上文雖然只列出3位傳主的6本傳記,但已經幾乎是筆者所能找到的全部了。
[13]. 1972年9月中日建交、臺日斷交之後,臺灣政府宣布「停止與日本的一切往來」,包括日本電影的進口和播放(根雨屋 2019)。因此,在筆者的童年,電影院中是不存在日本電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