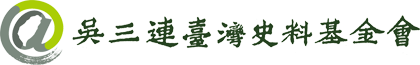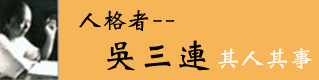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
《花蓮鳳林二二八》(花蓮地區) 張炎憲、曾秋美/主編
|
行過死蔭的幽谷──張七郎家族的動人故事
文/張炎憲
「我 雖 然 行 過 死 蔭 的 幽 谷 , 也 不 怕 遭 害 ,因 為 你 與 我 同 在……」
─聖經‧詩篇23:4
一、心中的許諾
一九九○年十二月八曰,我參加台北市懷恩堂所舉辦二二八平安禮拜。懷恩堂牧師周聯華以生澀的台語佈道,濟南長老教會牧師翁修恭則以華話講道。看似不協調,其實是呼籲台灣社會消解對立、相互理解尊重。其中最令人感到意外與感動的,是張玉蟬上台的見證。她說起花蓮鳳林張七郎父子三人被國民黨軍警逮捕殺害的往事,以及張家如何在困頓悲慘中堅強再起的艱難過程,說到辛酸痛處,句句令人落淚;但她語帶堅毅、充滿自信,不自怨自艾也不怨天尤人,那種不向命運低頭的精神更令人動容。她的一席話訴說了張家的苦難與悲痛,卻控訴了統治者的殘忍不義。
這一幕情景深印在我的心中,堅定我追究二二八真相與責任歸屬的決心。我心中默默許諾,一定要拜訪張家,留下真情的紀錄。一九九九年四月間為了協助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研究計畫,才得償宿願,趁著張家舉辦四十二週年的追悼會,訪問到張家家族。回到台北後,本想著手整理並計劃進一步修訂補足,卻因二○○○年五月,受命擔任國史館館長而中斷,八年任職期間,時常記掛此事,卻只能將許諾留在心底,等待機會予以兌現。二○○八年五月卸任後,重新過著自由的日子,我想是該要完成宿願的時候了,於是一面整理舊稿,一面重啟訪問,著手出版計畫。
這次重新訪問,最令人興奮的是訪問到張依仁。依仁長期避居巴西,回到台灣後也很少跟外人接觸,更絕口不談往事。也許是時代不同、氛圍改變了,也許是年歲已大、心境改變了,也許是上帝旨意,他終於接受訪談,說出昔日往事。我雖然期待他說出心內話,卻不忍心逼問,唯恐回憶會帶來傷心、憤慨與不悅,而再次傷害他的感情。
經過二十年漫長的等待,終於訪問到張家重要成員,完成心中的許諾。我心存感謝之外,對張家家族能夠熬過苦難留下證言,見證台灣人的滄桑與榮耀,更覺意義深長。
二、從台灣西部到東部的開拓者:張七郎
一八八八年張七郎出生於新竹湖口,排行第七。父親張仁壽是位漢醫,從湖口遷居新竹市內行醫。此時馬偕來到新竹傳教,仁壽有機會認識馬偕,終而受洗成為北部長老教會第一代的傳教士,並學到馬偕的拔牙術和西醫知識,從此雜揉漢醫和西醫兩者之長行醫濟世。
張七郎自公學校畢業後,因基督教信仰的關係,曾前往廈門英華書院就讀五年。英華書院是英美教會人士創立的學校,注重英語教育,他在此習得外文能力和西方近代知識。一九一○年,張七郎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學期間,一九一三年四月就與一八九二年出生、台北第三高女畢業的詹金枝結婚。
一九一五年醫學校畢業後,張七郎到基隆鐵路醫院服務,一九一六年轉往淡水開業,創設「仁壽醫院」,以紀念父親。一九二一年,張七郎舉家遷往花蓮鳳林,在此定居開業。張七郎為何選擇前往鳳林?據說可能基於兩個因素。一是接受在當地執業漢醫的五兄張逢年的建議,鳳林尚無西醫,居民需要醫療服務。其二則是受到馬偕在偏遠地區行醫傳教的精神感召和啟發,於是張七郎懷抱著理想與熱情,將「仁壽醫院」遷移東部開拓。
張七郎敢前往如此偏僻的環境執壺行醫,足見其眼光膽識、深具冒險犯難、開創事業的開拓者精神。對他而言這是人生重大的轉折,是向未知的挑戰;對東台灣發展而言,是漢人進入拓墾的重要事蹟。
鳳林「仁壽醫院」的患者遍及花蓮市以南至壽豐、豐田一帶,包括福佬人、客家人、阿美族人和泰雅族人等。張妻詹金枝雖具助產士資格,卻因醫院繁忙,甚少出外接生,都在醫院服務。夫婦兩人樂善好施,對患者照顧週到,甚至不拿窮者的醫藥費,其名聲逐漸遠播,獲得遠近民眾的愛戴。
張七郎在事業上穩定發展之後,更邀集新竹州的客家鄉親到鳳林一帶開墾定居,連所收養的養女,在其婚嫁之後也都將其安置在張家周圍的土地上,鳳林逐漸成為客家人的聚落。家業穩固、名聲遠播之後,張七郎已是東台灣數一數二的重要人物。
三、跨越台灣、日本與滿州:宗仁、依仁、果仁
張七郎接受日式現代教育、經常出國遊歷,又因教會關係時常接觸英美文明,深知台灣子弟要與日本人爭一席之地、提升地位,必須接受高等教育、拓展視野汲取新知,因此逐一將子女送至日本留學。
長子宗仁於一九三二年台中一中畢業後即到日本,一九三六年進入日本醫科大學醫學部,一九四○年畢業並取得醫師執照。畢業後返台結婚,又帶著新婚妻子前往日本東京執醫。次子依仁在一九二六年送往日本就讀小學,一九三二年進入東京錦城中學校,一九三七年畢業。三男果仁於一九四一年,淡江中學校畢業後也隨即赴日,就讀於東京齒科大學。
由於鳳林地屬偏遠,交通不便,學習環境欠佳,張氏子女除了長男宗仁和長女秀惠之外,全都曾去長老教會設立的「淡水中學校」就讀。淡水中學為長老教會所設,是當時西方文明與進步知識的傳播據點,張家將子女送往就讀,是基於馬偕的淵源及信仰關係,也有追求文明新知的目的。
一九○五年之後,日本勢力侵入中國東北,一九三二年更扶持滿州國成立,在建立五族共和、王道樂土的西進政策下,日本人紛紛移入拓展。台灣人因身份特殊,具有日本國籍又懂數種語言,容易在複雜的族群之間生存發展,因此也有許多人士前往滿州國,去異地建立基業。
張氏子弟最早前往滿州國的是次子依仁,約一九三八或三九年抵達,進入滿州醫科大學就讀,畢業後於一九四四年通過考試取得醫師許可證,進入阜新煤礦醫院執醫。一九四三年,隨著戰爭局勢惡化,張宗仁帶著妻子及兩個幼子舉家遷往滿州國,在奉天省海城縣開設醫院,也以祖父「仁壽」之名稱之。三男果仁與宗仁一起前往滿州國,一度進入長春大學附屬醫院工作,後至海城「仁壽醫院」協助。
張家兄弟三人從台灣到日本讀書,再到滿州發展,正是台灣人因應時代變化,胸懷壯志,勇敢跨越國界、力圖發展的表現。
四、終戰初期:張家鼎盛的年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台灣進入另一個時代。台灣人期待新時代的來臨,能帶來新的氣象,從此脫離二等國民的命運,步入台灣人治理台灣的時代。
張七郎在終戰初期,寫下許多慶賀的文字,並籌建磚造牌樓,顯見歡欣鼓舞的心情。這正是當時許多台灣人的寫照,希望奉獻己力,建設新台灣,於是許多人參加公共事務、投入選舉,企圖改造台灣。終戰之初,張七郎為了使鳳林子弟有更好的受教環境,趁國府接收之際,向縣政府申請籌設縣立鳳林農業職業學校,並擔任創校校長,一九四六年七月更進一步改為鳳林初級中學,使得鳳林附近一帶的子弟有機會可以繼續升學。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張七郎當選花蓮縣參議員並被推為議長;十月三十一日當選制憲國代代表,十一月上旬到中國南京參加制憲國民大會,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才回到台灣。憲法的制訂是中華民國憲政史上重要的一頁,表示國民黨政府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結束,進入憲政時期。
在新時代的趨動下,張七郎希望三位兒子從滿州回到台灣,共同建設新台灣。當時中國東北的政局也日益混亂,國共相爭不息,張家兄弟乃放棄多年辛苦經營的病院,先後經陸路、海路輾轉回到鳳林。
一九四六年夏天過後,三個兒子先後抵台,果仁及依仁又陸續結婚,張七郎非常欣喜,重擔也有人分攤,他將仁壽醫院的診療工作交給長子宗仁和三子果仁,鳳林初中的校務也交給了宗仁,自己則專心於政治事務。張七郎在兒子相助之下,事業版圖擴張,不只是東台灣舉足輕重的人物,更是全台聞人,也因此埋下日後被害的潛因。
在家族團圓喜悅時,張七郎其實已經體會到政局的不安、人心的浮動。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筆記上摘錄當時台灣流行歌:「轟炸 驚天動地;收復 歡天喜地; 接收 花天酒地;政治 黑天暗地;人民 喚天叫地」,又指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接收花蓮港,十六接收鳳林,爾後嗟嘆風聲街頭巷尾、智愚各般異口同音,鳴呼!今日島民之罪愆何可銷滅,犬去豕來,台灣建設徒聽空音」。這時他已察覺國民黨政府的接收不當,已使台灣陷入苦況。他在議會中也曾直言力爭,為民請命,但不被接納,反而預埋日後被屠殺的原因。
五、二二八大屠殺:父子三人遇害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台北因查緝私煙,長官公署處置失當而引爆二二八的抗爭。國民黨政府不顧台灣民意,反而視民主改革為叛亂,將參與民眾視為暴民。當時身兼國民政府主席、國防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總裁的最高權力者蔣介石下令派兵來台鎮壓,造成台灣菁英與民眾死傷慘重。
三月八日國民黨軍隊登陸基隆之後,立即進行逮捕槍殺的鎮壓行動。西部情勢稍緩之後,軍隊在四月一日開抵花蓮,隨即在祥和的東台灣進行一場慘絕人寰的家門屠殺。
四月四日下午鳳林人士設宴招待駐軍,表示迎接之情,張七郎罹病在山下住家休養,由長子宗仁代表前往。宴畢,晚上七點多鐘,軍警先至街上仁壽醫院騙走張宗仁,說是多位士兵於宴會後上吐下瀉需要醫治,請其多帶藥品前往治療;不久張果仁從外面回來,一路人馬立即進門將其綑綁、強行帶走。約是同一時間,另一路人馬則到山下,先在張家四周佈置機關槍和哨兵,層層監控之後,進門綑走張七郎、張依仁父子,出門時,張七郎以客語對依仁說了一句「子孫可憐」,成為父子最後對話。
父子四人被帶往軍隊駐在所,隨後依仁被單獨帶走,其餘三人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則於當晚深夜,遭槍殺於鳳林近郊的公墓,屍體被推入兩窟,一是張七郎、張果仁,張宗仁單獨一窟,以土草草掩埋。
四月五日,天才濛濛亮,果仁妻張玉蟬從街上奔回山下,欲向張七郎報告宗仁、果仁被捕事,卻得知張七郎、依仁也在前晚同時被捕。詹金枝隨後岀到街上醫院,吩咐媳婦殺雞做好四個便當,帶往駐軍處,卻被退回三個,只留一個便當,她心覺蹊蹺,卻不得其詳。同一時間,有位兵仔到仁壽醫院告知昨晚有張家三人在公墓處被槍殺。詹金枝回來家裡,得知此事,判定三人確已罹難,隨即召集近親外出尋找。下午四點多才在公墓找到埋屍之處,但因當時戒嚴,又沒帶搬運工具,只得返家再商量。張家派人前往警察局商量欲運回遺體,警察不敢允准。張家只好於次日清晨偷偷前往運回。
四月六日天未亮,詹金枝外甥詹德院、詹益謙等三人駕著牛車前往,將遺體搬上牛車並覆蓋芒草,走山邊小徑奔回到山下家中。據聞牛似也感到恐怖殺戮的氣氛,一路狂奔,無法駕馭。屍體運回家中,父子三人皆雙手反綁,穿著只剩內衣褲,外衣和隨身物品全被剝走,全身血污。遺孀們一一為死者清洗更衣,檢視遺體,發現三個人各中兩發子彈,從背後往前射穿胸膛,宗仁的臉上還有密密的槍刀割痕,且右手腕骨折;果仁的腹肚被槍尾刀刺破,腸子外流,是母親詹金枝親手將腸子塞入腹內,重新縫合。
四月七日,在鳳林教會牧師徐復增的主持下舉行簡單告別式,三人遺體隨即合葬於「太古巢農園」內,墓碑上刻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酒郊原 主後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屈死」。題字者是張七郎長兄張采香。當天參加告別式的都是家人親戚,其他人多不敢前來,會場彌漫著肅殺、哀傷的氣氛。
張七郎父子三人遭害不僅是遺族永遠的哀痛,也是台灣人苦難的共同印記。
六.支撐家族走出苦難:詹金枝
詹金枝在一夕之間失去丈夫和兩個愛兒。做為妻子,做為母親,怎能忍受這種打擊?父子三人去世,留下三個寡婦和五個孤兒,她們要如何生存下去、如何走出苦難,迎向未來?
張家面臨困頓崩潰之際,詹金枝以無人可比的堅強,勇敢承擔苦難,帶領兩個年輕守寡的媳婦,走出陰暗的幽谷。她的堅忍、毅力與執著凝聚了張家人的向心力;她對主的堅定信仰化解了哀愁與悲憤,主愛的力量支撐張家人度過灰暗,迎向未來。
張家子孫的回憶裡,詹金枝極為威嚴,有時冷酷得不近人情,常常叨念責罵,缺乏溫情鼓勵,連外人都敬畏三分,稱她「憲兵隊長」;但是她對教會和需要幫助的人,卻又好施奉獻,慷慨助人。她對家人要求高、管束嚴,對外則是仁慈寬宏,展現張家的大家風範。
詹金枝是凡人,必有軟弱的一面,但是她的哀傷只能在深夜獨自向主訴說。每天晚上她在自己的房內,禱告、吟唱聖詩,淒涼悲切的聲音,穿過安靜的夜空,每個角落的張家人幾乎都聽過,但沒有人和她談論她的悲傷,她也從不輕易說出內心的感受。每天早上,她到墓園或坐或站,面對墓碑有時喃喃自語,有時默默無言,也許是在跟丈夫和愛兒對話吧?告訴他們家裡最近的情況或是訴說對他們的思念。到底她說些什麼?她從來不說,也沒人問過。
詹金枝生活樸實,對子孫品行要求嚴厲,極為重視子孫的教育,不惜賣屋花重金讓子孫出國留學。她說:「生活、金錢都是身外物,讀書為了要出國,不要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掉。寧可做美國奴,也不要做中華民國的紳士。」詹金枝為了保全張家命脈,寧可忍痛讓心愛的子孫個個遠離身邊,她還說:「萬一她死了,不用通知孩子們回來。」深怕名列黑名單的子孫回來而遇害,寧可冷清走完人生。
七、新生代的再起:文滿、安滿、至滿
安滿畫過一幅水墨畫,最能表現出祖孫三代的情境。一個大石頭上長出三棵樹,磐石就是祖母詹金枝,長得挺直的是文滿,表示他的人生較順遂,另一棵稍微歪斜的是至滿,最是扭扭曲曲的則是安滿;歪斜扭曲表示人生路程的曲折和艱困。畫中有三座山,山中有房子,山是祖母和兩位媽媽,山下老家就在這三座山的環繞維護下佇立著。另外飄渺遠逸的三座山,則是逝去的三位親人。
磐石怎能長得出樹?但那確是生活的寫照,若非祖母堅硬得像磐石一樣,三個幼子無法成長茁壯,祖母是他們最大的支柱。對三個孩子來說,他們共有三個媽媽,祖母加上兩位親身母親。三個媽媽在一夕之間,都從醫生娘變成了農婦,她們要面對經濟困境,勤儉持家;三個媽媽的性格不同,對孩子們卻是不分彼此,相互愛護教導,正因有三個媽媽辛勤的供養、教導和呵護,他們才能成長壯大。
張家新生代在三位女性的養育下,在苦難中逐漸成長、走出陰暗,克服外在環境的困阨以及內心的創傷,重新出發,在事業上均有成就。文滿,淡江大學化學系畢業,之後到美國留學,獲維吉尼亞州立大學化學博士學位,現居美國。安滿,逢甲大學銀行保險系畢業,在國中任教,現已退休。至滿,文化大學體育系畢業,留學美國,獲愛荷華大學的體育博士學位,返國之後,曾出任教育部體育司司長,現任教於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八、從台灣到美國、巴西:依仁、秉仁、存仁
依仁被關三個月之後獲得釋放,回到家裡的翌日,帶著妻子和秉仁到達淡水,從此在妻子娘家附近開業行醫。因父親張七郎曾經在淡水開業,患者都知道張家,依仁待人親切、談吐風趣,又因醫術頗佳而有「囡仔仙」之稱譽,因此患者很多,常常看到夜晚仍然無法歇息。
依仁到淡水開業,逃離二二八的苦難現場,卻躲不開國民黨的干擾,特務無孔不入,幾乎每個星期都在深夜十一、二點登門,翻箱倒櫃、問東問西。這種形同恐嚇的舉動,讓依仁心驚膽跳,而有隨時被捉的恐懼。
依仁支助秉仁、存仁和文滿大學畢業,在秉仁、存仁出國後,自認為對弟弟和侄子的責任已了,應該為自己和妻小著想,決定遠離台灣。一九六一年,他託人幫忙拿到護照,又以赴日看病的理由,獲得日本簽證。到東京之後,暫時住在蹈仁家,本想在日本病院工作或自己開業,但在日本居留不易又考量子女教育問題,蹈仁勸他前往巴西。一九六三年他設法取得巴拉圭的簽證,坐船經美國到達巴西,登陸之後,經朋友幫助,設法進入巴西北部的教會醫院服務,但因一直無法順利取得巴西的開業執照,只得屈居於教會醫院,領取正式醫生十分之一不到的薪水,生活艱難。
一九六四年,依仁之妻帶著與子女三人從台灣經日本,抵達巴西聖多斯(Sandos)團圓。患難家庭能在海外團圓,找到棲身之地,真是難得的幸福。但國民黨的爪牙仍然伸展到巴西,駐巴西的副領事甚至向巴西當局密告依仁是危險人物,要將他驅逐出境。逼使張依仁不得不離開家庭,逃至窮鄉僻壤,甚至不敢與家裡聯繫,在外流離七、八年之久。在此期間,巴西家中的妻小也因財源斷絕,存款用盡,醫師娘和千金小姐不得不變成躲警察、被搶挨打的小販。多年後,才能勉強開出一間小店面,販賣雜貨賴以維生。在北部叢林逃亡七、八年之後,依仁回到了聖多斯與妻兒同住,從此在家協助妻子,未再開業執醫。訪問時,他無限感嘆說:去巴西是他人生的最大敗筆,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兩個女兒都順利從醫學院畢業,獲得醫師資格。
秉仁,淡水中學、台灣神學院畢業後,曾在新竹桃園一帶佈道,後到美國留學,後被教會派往巴西佈道,比依仁還早三個月抵達。存仁,師大音樂系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後赴巴西傳教,娶巴西人為妻。兄弟三人在台灣遭逢家變之後,到日本、美國、巴西發展,重新開展新的人生。然而,當他們敬愛的母親詹金枝於一九八二年去世時,他們無法取得回台簽證,如期趕回台灣奔喪,成為他們心中最大的遺憾。
九、山下太古巢的守護者:張玉蟬
張玉蟬,一九二九年出生於新竹。六歲時被賣到張家當養女,因為性情溫和體貼、吃苦耐勞又聰慧,頗得張七郎夫婦的疼愛。鳳林公學校畢業後,入學台東高等女學校,後轉學花蓮女中,一九四六年初畢業。
她曾經想過放棄學業,但在父親溫暖鼓勵下,決意完成學業,不負父親的期望。她對父親的栽培之恩,一直感謝在心,對父親的作為,更心存尊敬。
張七郎夫婦因疼惜張玉蟬,想留她在身邊,於是將她許配給三子果仁。戰後果仁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從滿州國回到鳳林,十一月兩人完婚。張玉蟬從來沒想過會嫁給張家子孫,果仁長期在外,與她很少接觸,雖無男女感情可言,既是父母親之命,便順從結婚。張玉蟬本來是張家養女,完婚之後變成媳婦,她對詹金枝既是女兒,也是媳婦;詹金枝對她既是母親,也是婆婆。這兩種身分使得她對詹金枝有著尊重、服從、畏懼和親近等等複雜的感情。
果仁被害時,張玉蟬年僅十九,懷有四個月餘身孕,一九四七年十月產下遺腹子張至滿。至滿因與祖父年歲相差一甲子,一出生就沒有父親,而且從小身體就虛弱,阿嬤詹金枝對至滿懷有特殊感情,決意親手將他扶養長大,特別鍾愛他。所以在三個孫子中,至滿和阿嬤最為親近,從小和阿嬤一起睡覺,甚至一起泡澡,也只有他不怕阿嬤、敢跟阿嬤逗笑。
張氏父子三人去世後,山下就只住著三位媽媽和三位孤兒,雖然有孩子的笑聲,但氣氛是沈悶的、悲傷的。婆婆年歲大不堪勞動,伯母秀氣無法適應園裡工作,只能負責屋裡工作,農園裡的工作就只能落在張玉蟬身上。農園工作既粗且重,天天拔草、整理園地、種植果樹及採收販賣,此外還要設法養雞養豬,貼補家用。如此生活日復一日,何時能得解脫?
一九五二年間,張玉蟬與鳳林教會傳道師的弟弟陳喬格相識,進而相戀相愛。兩人請求結婚時,詹金枝盛怒不能同意,經張玉蟬苦苦懇求,終於答應,婚禮卻安排在四月四日與張氏父子追思禮拜一併舉行。陳喬格搬入張家一起生活,但因不能適應張家的習慣,不堪阿嬤的嚴格要求,數度離家出走。為此,母親詹金枝數度逼她做出選擇,要丈夫或者稚子至滿。張玉蟬夾在敬愛的母親與親愛的丈夫之間,左右為難,不知所措。最終她不忍已無父親的至滿再失去慈母,於是選擇犧牲自己和女兒惠操,離開深愛的丈夫。
惠操出生於張家、長於張家,雖然張家上下視她為親人,三個哥哥對她疼愛有加,但是一直無法獲得祖母的認同和疼愛。特殊的身世和成長背景,深刻影響她的性格和思想。母親張玉蟬雖然竭盡所能,付出所有的愛,卻無可避免她在成長過程中所受的傷害,為此至今仍常感抱歉。歷經成長的苦悶,惠操終於跳脫困頓多年的心牢,更能諒解、體貼母親的無奈和辛勞,也由於她的支持和鼓勵,張玉蟬才能挺身為張家見證申冤。
離婚後,張玉蟬帶著惠操仍住在山下,辛勤工作,照料住家。孩子們長大後,陸續結婚成家,山下老屋只剩張玉蟬陪伴詹金枝。詹金枝生病臥床,直到一九八二年過世,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一手照顧。聽到母親臨終時說:「妳服侍我這麼多年,我十二分的感謝,十二分的滿足,上帝會祝福妳。」一切的付出都得到了安慰。
詹金枝決定將山下太古巢農園交給張玉蟬,是肯定也是一種託付,或許是認定張玉蟬會一直守住這個老家、這片山園。如今張玉蟬仍時常獨自守在山下的家,不願也不忍離開,因為這裡記憶著她一生的曲折際遇,埋藏著她的快樂與悲傷。
十、真相與公義
張家的苦難,見證著統治者的殘暴不仁及庶民大眾的無辜和無奈。
二二八屠殺前,已有特務長期到張家監控,事發時也是他率領軍人到張家抓人,當天還睡在張家,直到天亮才離開。葉蘊玉(宗仁妻)和張玉蟬拿現金給他,拜託他營救,他卻說這是南京的旨意。那到底南京是指誰呢?
有人說是張七郎批判花蓮縣長張文成,兩人有過節,縣長乃藉機報復。但張七郎身為制憲國大代表,非泛泛之輩,縣長的密告就能處置他嗎?沒有更高層的權力者同意,誰敢動他?
事發後,詹金枝曾書寫訴冤狀,獲當時台灣高等法院檢查處的批示:「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等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拒捕遭擊斃一案前經前台灣警備總司令電准備查在案」,事實上,張七郎為制憲國代,哪裡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的證據何在?被捕時四人皆未抵抗,任由軍人綁走,若是拒捕遭擊斃,應當死在被捉現場,怎會埋屍公墓?這份批示充分顯示當時軍人未據實以報,反而誣蔑事實,圓謊卸責;而法院僅以軍方之說裁示,顯見法官沒有人權觀念,未站在人民的立場,公正判決,只是替統治者辯解,這正印證「法院是國民黨開的」的說法。
二二八真相至今尚未釐清的是:被屠殺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以及誰下令屠殺的?為什麼台灣菁英幾乎在同一時間遭到被逮捕、槍殺的命運?
觀諸事後國民黨政府的處置方式,高陞鎮壓屠殺台灣民眾的官員,對台灣民眾則不予撫卹,反而嚴禁談論二二八,使二二八成為台灣最大的禁忌。種種後續作為充分表達國民黨政府對二二八的處理心態,認為這是叛亂、暴動,派兵鎮壓有理,而且死不認錯,加害者至今沒人站出來承認或道歉。
從國民黨政府處理二二八的態度,就可以理解張家父子為何會被殺害。張七郎在東台灣是數一數二的領導人物,兒子們也相當傑出,如果不殺一儆百,統治者很難在東台灣或台灣樹立威權。導致張家父子三人罹難的種種說法雖都有可能,但最重要的原因則是統治者歧視台灣人民,以報復與懲罰的心態,任意屠殺台灣人民,剷除領導菁英,以利建立獨裁政權。
二二八平反運動自一九八七年展開之後,已歷二十多年,台灣也已進入自由民主的年代,然而,轉型正義未徹底落實,加害者未得到應有的審判和懲罰,公理是非無從確立,過去統治者所造成的傷害便仍折磨著民眾的心靈,張家就是最佳例證。
十一、苦難與再生
張七郎父子三人被捕槍殺是世間劇痛,令人惋惜哀傷。但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事變之前家業蒸蒸日上,事變之後家道中落,存活的人要承擔死難者留下的未竟之業,忍辱負重教育下一代,堅強地活下去,這是何等艱難的路程。
張家父子一夕之間被害身亡,留下三個寡婦和五個孤兒。外有白色恐怖籠罩,國民黨情治特務無時不在監控,社會則冷漠對待,不敢伸出援手;對內需突破經濟困境、設法賺錢謀生,教養下一代、延續命脈。若非身歷其境,實在難於理解與體會,張家就是如此走過了風霜歲月。
張家族人各具強烈性格,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一個獨特的動人故事,他們的遭遇與感受雖有不同,但張家的苦難都深植心底,影響著他們人生的走向,雖然充滿波折,卻是台灣人一百年來身世與苦難的縮影。
張七郎生於滿清統治時代,在日治時代成為台灣菁英,來到花蓮鳳林開疆闢土,寫下動人的開拓者事蹟。隨著時代的轉變、視野的擴大,張家人壯志飛揚,宗仁、依仁、果仁三兄弟到日本讀書、到滿州創業,象徵台灣人的腳步已非侷限台灣一隅,而是拓展至東亞。
日本戰敗,國府接收之後,張七郎成為台灣耀眼新星,可惜在二二八大屠殺中,父子三人殞落。觀之後來的發展,依仁、秉仁、存仁和文滿的行蹤,竟又跨越台灣、美國與巴西,雖有被迫出走的無奈,卻反映出台灣人的眼界追求,已從東亞擴展至美洲。
張家在二二八遭受鉅大的的苦難,詹金枝以大家長的權威、堅定虔誠的基督信仰,帶領著子孫走過黑暗,迎向新生,這些動人的故事,正是戰後台灣社會的真實寫照。
本書出版終於完成我多年的心願,衷心期盼他們的奮鬥事跡,能讓大家更具信心,縱使在那麼黑暗的年代,那麼恐怖的年代,只要勇敢站立起來,面對、承擔苦難,總能行過死蔭的幽谷,再創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