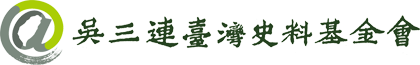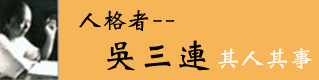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
《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 賴淳彥 著
|
蔡培火先生與我
1936年(昭和11年)我在東京東洋音樂學校(日本戰敗後改名東京音樂大學)學音樂。記得有一天該校畢業、主修小提琴的翁榮茂前輩來找我說:下禮拜六晚上六點,蔡培火先生要請在東京學音樂的學生和前輩們,在新宿東橫線東站餐廳開座談會並一起吃飯,翁前輩且說江文也兄、陳泗治兄、黃演馨兄、張彩湘兄、戴逢祈兄都會來,我隨口說我一定去參加。
當夜,翁學長以外的每一位都是初見面的,至於蔡先生是幾年前在霧峰攀龍先生的一新會舉行演講會時見過一次。首先由翁學長簡單介紹蔡先生,並說明今晚座談會的目的是要各位互相認識,今後在音樂方面互相幫忙,培火先生也很親切向大家問在東京學習音樂是否順利等等。江文也兄當時在日本音樂界是一位有名氣的作曲家,他向大家報告說,他的作品「台灣舞曲」如果在德國舉行的奧運大會入選並被演奏,今年就要去德國參加奧林匹克大會。張彩湘、戴逢祈和我都是在學校磨練中的學生,就沒有什麼話可報告。記得培火先生說:「我不是學音樂,但是喜歡音樂,喜歡寫歌曲。去年台灣中部大地震受災害非常,我也寫一首歌在台灣開音樂會募捐救災,我自己帶動聽眾一齊唱。」當時大家請他唱,他就不客氣唱給大家聽,在座的每一位對蔡培火先生這樣率直的表情非常欽佩和讚譽,每位也就不怯懦,被問什麼就坦白答什麼,也因此,大家覺得很暢快,吃了晚餐後一直到九點才散會。
我知道了伊勢丹百貨公司附近那家味仙餐館是蔡培火先生開的,就常去吃米粉湯,有時候也會碰著蔡先生打招呼聊聊才回去。當時味仙有一位在法政大學唸法律的學生叫做邱鴻恩(光復後回台南做檢察官)也在店內幫忙會計的工作,在味仙我從一碗米粉湯15錢(一角半)吃到我畢業時價到25錢。
快畢業時有一次,住在下北澤的黃演馨兄在家裡召集音樂界的台灣人士舉行親睦座談會,蔡培火先生也來參加,他按照通知信六點就到黃家,不過,其他人像翁榮茂、林澄沐、戴逢祈、陳南山(帝國音樂學院畢業後留在該校當講師教普通樂理)還有我,都遲到三十分以上才到。培火先生就破口大罵:「搞音樂的不守時間,你們的音樂會好才怪!快板彈成慢板可以嗎?不止音樂,在這文明時代不能守時間的人談不上是文化人,生活上要有規定的節奏才可算是現代人!」大家想不到見面就上了他第一課。首先陳南山兄(他年齡最大)說在東京要以音樂維持生活非常困難,想要到大陸去找些適當工作等,聽說江文也兄移住北京在北京師範學院教音樂非常受歡迎,現在熱心於作曲等。大家聽了南山兄的話才知道江文也兄現在住北京。
培火先生聽了並沒有回答,問我說:「泉生你今年是否要畢業?有沒有參加畢業演奏會?」我說:「可能會參加,但是要等到畢業典禮完後才能決定,日期可能在 4月初,場所在明治神宮外苑的青年會館,入場券印出來我會送給您。」他聽了非常高興,且說:「能參加畢業演奏會真不錯吧,應該多請些台灣留學生去為你捧場。」
黃演馨兄畢業於立教大學經濟系,在一家公司就職,學生時代喜歡唱歌,拜女高音柳兼子女士(上野音樂學校教授)為師有四、五年,修得非常好的男高音。他的太太是畢業於帝國音樂學院的女高音,也是柳兼子的好學生。這次的餐會有吃有談有笑,互相非常融和,到十點才散會。散會前培火先生吩咐大家幫忙黃太太整理一切才回家。
培火先生這種作風給我們年輕人更欽佩他,有老大的風格和有能力指導人,敢說敢為。
我的畢業音樂會定於4月3日在明治外苑的青年會館舉行,前幾天我親身把入場券送到味仙給他。音樂會我是前半場第五個節目,當我唱完進入後台時,培火先生到後台來看我。他首先跟我握握手,並說:「唱得不錯,恭喜你。音樂會完了後趕快到味仙來,我請你吃飯,我先回去在味仙等你。」
我的音樂會完了後,又要照一張紀念相,全部完了後幾位同學要我與他們去喫茶店再聊天,我婉拒說有事情要先回去,就趕到味仙去。當我進入味仙時,培火先生說:「我想要打烊,你怎麼現在才來!」我告訴他音樂會收場後的事情,他才息了怒氣,馬上叫人端東西出來,一盤炒米粉,一盤全魚,一盤白切雞,一碗湯,以當時學生的身份能有這樣料理享受,那是想也想不到的快樂事!他坐在我面前一直勸我吃,其實我不餓、吃不下,心內很感激,吃一點點就對他說:「非常感謝您請我這樣好吃的料理,可惜我現在不太餓吃不下去,真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讓我帶回去明天再吃?」培火先生說一聲:「好啊!」接下就叫店裡的人來,說:「拿 4個肉包和這些菜魚統統打包給泉生君帶回去。」
1939年(昭和14年) 7月我在淺草常盤座當歌手演出時,培火先生和吳三連先生賀我演出,送來兩個大花環放在劇場的大門口。改天我到味仙向他道謝時,他對我說:「很好,有事做能生活,不過淺草的地方民情低,比較複雜,流氓很多,尤其你在娛樂界出顯特別要注意。」想不到培火先生會對我講這樣關照的話,其實我的老師也對我講過好多次。
1940年(昭和15)年我考上了 NHK放送合唱團和日本劇場的聲樂隊,他知道了這個消息,非常為我高興。
光復後他住在台北市大安區,有一次我去拜訪他,他拿出來許多他所作詞曲的歌給我看,使我嚇了一跳。不是專門學過音樂的他,自己作詞配旋律成歌曲,而用來啟蒙奴根性重的殖民地台灣人。歌有「咱台灣」、「台灣自治歌」、「基督青年會歌」、「霧峰一新會會歌」等等,許歌都是為啟發台灣人的文化生活而作的,其他也有民謠風的歌曲和兒童歌。以七十年前殖民地台灣的狀態看,這些歌並不是為藝術而作,只是為著要推動台灣人的生活來做運動的清涼特效藥,也就是為著糾合台灣人反抗殖民政策的歌聲,鼓勵台灣人團結打拚的啦啦隊歌,糾正奴隸根性的刺激劑。培火先生雖然不是正派的音樂家,但是以一位業餘的音樂愛好者,能用他自修膚淺的樂理來作曲,引導當時的青年男女站起來,自覺民族的尊嚴和抗爭民權與自治的精神是可貴。
對培火先生的評論各有千秋,我認為他懂得文化是什麼,才能想盡辦法重視社會教育,關心生活的改良,幫助青年人的學業,無論怎樣看的確是一位先覺。他為了改良台灣語言的缺點與複雜,用羅馬字拼音的白話字來解決台語發音和寫作的問題,當時非常熱心推行白話字運動。可惜一般台灣人眼光看不遠,不瞭解白話字的好處,而且當時的日本殖民政府對改進台語的運動不但不關心,反而期待台語不久會自然消滅,白話字運動因此受阻礙。但是,近來因時代和環境的變化,本土意識的要求,自然而然對母語的觀念,說與寫的研究漸漸提高。假使當時大家眼光看遠一點,今天台灣人不必為講台語寫台語來操心,七十年前培火先生用羅馬字拼音講台語,可證明他對台語已有非常大的關心。
台灣光復後有音樂會他常來聆聽。有一次榮星合唱團在國際學舍舉行定期公演,他來聽,翌朝七早八早他來我家,以嚴肅的表情對我說:「我問你,你請客時有沒有考慮那位客人要請他坐在那裡?」我嚇了一跳隨口說:「我沒請客呀!」他說:「胡說!昨夜音樂會你是否請許多人來聽,這些人的座位是否有安排?」我:「招待客人的招待券不是我分配的。」他就說:「你是榮星合唱團的團長,該做的事情你要注意,正派的音樂在中國稱為禮樂,演奏(唱)者和聽眾都要以禮貌相處,不能馬虎,連座位都無法安排好,還有什麼禮樂要以禮貌相處,不能馬虎,連座位都無法安排好,還有什麼禮樂呢?」我忽然想出來「禮者,天地之序也」。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創辦人辜偉甫先生,他也嚇了一跳,原來發入場券的人把老先生的座位弄錯了。
榮星合唱團在榮星花園舉行二十週年團慶時,大概因為在野外舉行,許多有頭有面的名士多沒來參加,只有培火先生和小朋友有說有笑有唱,爺爺和孫子們在四月陽光高照、百花齊開的花園裡增添一幅和諧的美景。八十多歲的老人能夠與小朋友們在一起的光景在台灣的確未曾有。
敢言敢做,一生以身作則為台灣打拚的志士蔡培火先生,雖然他為台灣所作種種運動,沒完全按照他的理想實行,在台灣的歷史上,他的事蹟的確有價值且有需要永留下來給後代的台灣人做殷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