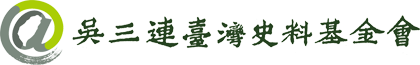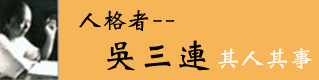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
《噶瑪蘭二二八》(宜蘭地區) 沈秀華、張文義/採訪記錄
|
文/沈秀華
第一次作二二八事件採訪,是九○年二月噶瑪蘭雜誌要製作二二八事件四十三週年專輯的時候。當我結束第三個見證者的採訪,正是一個陰冷飄雨的午後,這是蘭陽典型的冬日,我佇立站牌下等候公車,心裡有股清明的力量在說話,我願意以我的能力來認識台灣這塊土地。
曾經做過其他調查採訪工作,從沒像二二八口述歷史採訪,在過程中要面對更多的疑懼與傷痛。但是無論受訪者或採訪者都在這段互動中成長。受訪者從驚懼到信任、主動提供資料,甚至還成立宜蘭二二八關懷聯合會,這需要極大的勇氣。
在保守估計死亡人數達三萬人之多的二二八事件中,目前出面的受難者家屬只佔極少數,其中多數又為菁英者的後代。在生命價值不因階級有貴賤之分的理念 下,來自各階層受難家屬組成的宜蘭地區三一八關懷聯合會,正是鼓勵其他家屬勇於站出,也希望社會大眾更要關心那些當年沒沒無聞、不明不白就犧牲的受難家 庭。
至於我個人,不僅從訪談資料中,對事件延伸更多的思考,也實際「領教」口述歷史方法學的難處。
在台灣,口述歷史工作仍屬起步階段,未建立起可循的方法學。
在我們這次工作過程中,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記錄?以何種語言記錄?我們的受訪者幾乎都以閩南語口述,在目前閩南語文字系統未定,使用也未普偏下,到底 是該忠於訪談過程,保存其口語,或者為方便讀者閱讀而採用北京語系文字記錄。個人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遭遇極深的困擾,從最初直接保留其口語來完稿,又以北京 語文字改寫過二、三次,最後仍以初稿為底本,因應電腦打字無法顯示全部的閩南語用字,而作小幅修正後定稿。
經過反覆的討論、改稿後,個人仍然認為口語記錄方式,較能傳達訪談的情境,受訪者的形象與文字呈現間的距離被拉近了。因此我個人整理的篇章中,仍保有 閩南語言習慣和用字,當然這中間閩南語用字容有爭議,記音整理下,文句容有不完整,這些問題的顯現,是我個人目前能力下未能處理好的,卻是值得台灣歷史文 化關心者來深究。
檢視二二八事件,是認識台灣近代史一把極重要的鑰匙。當多位受訪者談及,台灣社會辦事塞紅包,是四五年中國官僚體制來台後才有的現象,我猶記得聽到此 話久久驚訝的神情。在觀念中,我以為那是台灣「固有文化」。瞭解台灣與中國首次深入接觸的經驗,幫助我們知道台灣過去是什麼?四十年來是什麼?未來要什 麼?並且釐清未來兩岸的關係。
主導二二八當時台灣民間力量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對中國政權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其內容、精神與要真正獨立成一個國家是有差距的,這是目前受討 論的議題。以士紳為主體組成的委員會與中國政權間是採取談判路線,而街上遊行、上山打游擊的又以普羅階級組成。因階級不同而有行動的差異,也許因主導時局 的不同,歷史也有不同的結局。當然,歷史無法重來,也無法假設,然而這樣的反省,是否可提供目前仍有路線之爭的反對陣營一個思考點?
另外二二八當時台灣民間組織、動員能力之快速,其模式如何?與日據時代的組織有何關連?這股力量被打壓後,是真的煙消雲散,或在民間社會內轉換成其他 勢力、力量在伏流?並且對後來的反對運動在意識、組織上有何影響?若從歷史的縱向來觀察台灣反對運動,上述的問題意識值得再釐清。
一次訪談中,一位受難家屬無法釋懷父親受難後,母親與一名男子在生活上互相照顧的事實。由這位受訪者無意中流露的神情,我開始注意起女性在二二八事件 中的角色。當時的受難者幾乎清一色為男性,他們的妻子,這些年輕守寡的女子,在父權社會下,如何孤力扶養子女?如何安慰自己一顆驚懼、寂寞的心靈?
見證者蔡燮基的母親在軍隊深夜包圍住宅,找不到她丈夫,抓走她的兒子後,變得精神異常,常常喊:「兵仔來啊!兵仔來啊!」陳成岳日籍遺孀絕口不提二二 八,怕見生人,怕見人多。受難者林蔡齡的兒子林哲信,提起他已辭世的母親:「伊真堅強,但是二二八事件再怎麼平反,也無法度彌補阮老母一世人的傷心。」張 雲昌的遺孀張楊純咬緊牙根把孩子帶大,四十年來不談二二八,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插」政治。賴阿塗的妻子,在先生受難後,拒絕別人好意要來分養她的孩子, 也拒絕再嫁的機會。
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的遺腹子郭勝華女士,靠著相片來認識她的父親;賴阿塗的長子賴辰武先生,每次從遠遠的路上,望著用紅磚塊做記號的父親的墓,心中有著不滿;死裡逃生的林金春先生,自己避著不敢與朋友交往。
無論從女性角度或是遺族立場,每一篇整理都是口述者一生難以彌補的痛。個人深切認為這種口述工作,不僅幫助我們認識事實,也提供豐富的研究、創作體 材,將來二一八研究,不只是歷史學家的責任,更需要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甚至文學家的參與。感謝一年多來受訪者對我們的信任與協助,這份記錄的完 成是建立在你們的血淚上,也謝謝張炎憲老師,出於對台灣的愛、對史學工作的認知,熱誠給予我們指導。一年來與文義兄的合作,是個真誠的互動,另外要提起的 是,若沒有噶瑪蘭雜誌多年來在宜蘭持續挖掘二二八事件,我們的工作一開始也不會如此順利。最後要感謝我的父母,在我「算電線桿」的這半年多來,給予我最大 的包容與空間。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