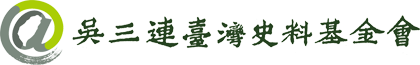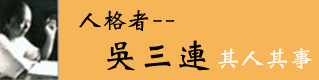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
《回首來時路 ─陳五福醫師回憶錄》
張文義整理記錄
|
回頭看來路
文/陳五福
我的出生地──羅東,位於蘭陽平原上,東邊濱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三面環山。而蘭陽平原自來米產豐富,西側為高聳的中央山脈所圍繞,其間太平山所盛產的「紅豆杉」(紅檜)被視為台灣珍寶。南端由於山勢陡峭,形成斷崖,而與花蓮為界,北面則以三貂嶺與台北為鄰,地理及民風,自成一格。
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離陸地不遠的海中,坐鎮著龜山島,此島以狀似海龜而聞名,且古來即流傳著各種傳說。其附近海域及蘇澳港所出產漁類頗為豐富,長久以來滋養著世世代代的人們。
記憶當中,平原儘是稻田,而散佈其間的綠色竹圍,包裹著紅磚砌成的農舍,相映於田野、水面間,宛如一幅圖畫。而牛總是默默地服從其主人的命令,勤勞地鋤田、工作。遍佈田間的流水與圳溝,各式魚蝦浮游其間,悠然自在,而田螺最喜歡於田間、水道旁休息了。回想兒時景況,著實百感交集。
基本上,父親半商半農,成天忙於工作,而母親為著家事及照顧九位子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未歇息或喘一口氣。由於兄弟姊妹的年齡,相差各兩歲,所以大哥、大姊均能代替父母照顧弟妹,同時,一個接著一個,陸續上學就讀。
日治時期的公學校,功課至為輕鬆,不像現在壓力這般沈重。下課回家,或獨自或三五成群玩著自已以木頭或竹竿製成的各式玩具。有時,則帶著小狗於田間小道相互追逐。這快樂的時光,與所謂升學壓力及課外補習,完全絕緣。然而,待升上高年級時,便漸漸注重課業了。
尤其考上中學以後,生活幾乎完全改觀,甚且排有軍事教練課程。進入高等學校時,日本軍國主義方興未艾,剛開始雖然影響不大,但是,隨著戰局的緊迫與需要,日本政府對其所屬殖民地逐漸嚴加管制。不僅其內地(日本本土),包括韓國、台灣等地,無論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乃至思想精神方面,積極地實施動員、統制政策。而在「大東亞戰爭」的國家威權體制下,有關人民的基本人權、自由,非但受到壓迫、箝制,甚至被視為「非國民」的危險思想,一旦顯露異於官方言論,立即嚴加監視或逮捕。也就是說,基於大日本帝國的「雄飛海外」政策,人民只是國家的財物而已,且必須絕對服從國家命令,甚至犧牲、放棄個人生命,根本無個人幸福與人格可言。
大學二年級(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於焉開始,同時引發全球性的世界戰爭,而世界亦為之分為東西兩大陣營,彼此互相殘殺、蹂躪。台灣身為日本的殖民地亦不能倖免,年輕人一批批地受徵召被送往海外戰地。有些人於途中即葬身海底;有些人雖幸運安抵目的地,卻客死異鄉。而這一切只不過為著「天皇萬歲」,以及抽像的日本帝國而已。
為著摧毀敵人的戰鬥意志與力量,數以千計的空軍,夜以繼日地實施轟炸,更慘絕人寰的是,化學武器被大量投入戰爭,以求得勝利。由於所有物質均投入戰爭,而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則無不陷入饑餓狀態當中。
戰爭雖然結束了,人類亦付出相當代價,同時亦覺悟到人類的愚蠢,歷經這麼悲慘的戰爭,殺戮了多少生命,破壞、損失了多少地球資源,究竟獲得了什麼?人類雖具有理性,且自誇為萬物之靈,針對其所犯下的罪過,未必比野獸高明多少。
戰後五十年來,全球各地,規模大小不一的衝突、戰爭,不計其數。隨著科技的發展,各國擁有的核子及生化武器,其存量足以毀滅世界的主要都市數十次以上,且其各式飛彈,只要按鈕,即能摧毀對方。其實眼前的和平,如累卵般脆弱,戰爭似乎有隨時發生的可能。
終生堅持和平主義的史懷哲,一直呼籲人類要互相尊重,敬畏生命,建設和平的世界。他說:「我是芸芸眾生當中的一條生命。」也就是說,我要生存,你也一樣要生存,你我必須互相支持,使得生命充分發揮其存在的價值。我們要體會造物主創造宇宙的美意,所有的生命,無論大小生物,都必須尊重其存在的權利。而且,人的生命是有時空限制的,對自己的生命,我們只有使用權,並沒有所有權。基於此,人類更加需要相互扶持、共勉,使得人性能往良善方面發展。
數十年來,從事眼科醫療及盲人社會工作,耗損了不少體力,且平日亦無寫日記的習慣。記得二十餘年,好友曹永洋先生即有為我作傳的建議,但為我所拒絕而作罷。六年前,他又鍥而不捨,我仍然不答應。但是,看他一片熱誠,一直拒絕,終究於心不忍。於是在我的祕書林惠蓮小姐的全力提供相關資料下,他先後提著行李兩次到「慕光盲人重建中心」,體會盲生的生活情形,並對老師及盲生進行採訪,俾便蒐集資料。其頗受好評的《噶瑪蘭的燭光──陳五福醫師傳》即在這種情形下完成,並於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付梓。
其實,撰寫傳記,並非易事,尤其是自傳或回憶錄式文章。因為就我個人的想法,即有三種不同的我:一、自己所認識的我;二、別人所看到的我;三、我在想像對方所瞭解的我。這三種的我,並不一定會一致,而到底哪一個是真實的我,也很難界定,其困難處在此。然而,既然決定要回憶、口述過去的我,就必須真實、坦然地面對,如此方能呈現真正的我。
對我這一生,原本認為有《噶瑪蘭的燭光》一書即已足夠。但在偶然的機會下,出生於台東的張文義先生,以其研究台灣史的經驗,曾建議我以口述方式,由其錄音、整理,而為歷史留下紀錄,俾為後人提供參考。這本回憶錄即在此因緣下完成。
我雖然出生於台灣東海岸偏僻的鄉下,但台灣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且後代子孫要長久居住的島嶼,同時,我們都受到它的庇蔭與栽培,對其付出關心及愛護,乃天經地義的事情。此後,我們要為這個島嶼奉獻更大的心血,建設和諧、安定的社會,更要讓所有住民分享具有高度文明的家園。
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