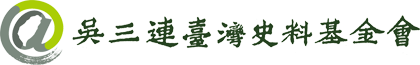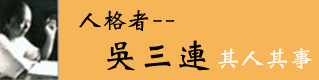|
《噶瑪蘭二二八》(宜蘭地區) 沈秀華、張文義/採訪記錄
|
文/張文義
(蘭陽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2011年1月13日下午正在學校處理教務工作時,無意當中接到「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陳朝海先生打來的電話,電話中直接說明當年〈19年前〉由自 立晚報文化出版部出版的《噶瑪蘭二二八》一書,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決定和其他三本書一起重新出版。接到這種消息。內心似乎沒有特別感受,但又立即引起當 年和沈秀華小姐一起採訪受難者家屬或見證者時的種種情形。因為我們的採訪、紀錄才有這本不太成熟的《噶瑪蘭二二八》,後來也和受難家屬一起籌組並成立「宜 蘭縣二二八關懷聯合會」,從此隨著台灣社會對二二八事件的開放,以及家屬勇敢地走出歷史陰影,逐漸走上盛行一時而屬於全台灣二二八受難家屬的二二八運動。
回想1990年前來宜蘭工作時,曾經到設在羅東而由後來擔任宜蘭縣長的劉守成夫婦主導的「噶瑪蘭雜誌社」拜訪,並在那裏認識了沈秀華小姐。之前,就知 道「噶瑪蘭雜誌社」出版的《噶瑪蘭雜誌》針對二二八事件有做出一些相關報導,但並沒有直接採訪受難家屬。雖然如此,記得當時即有意請沈秀華小姐一起來做宜 蘭的二二八口述歷史工作。
之後,筆者進入設在宜蘭縣立文化中心的「文獻小組」工作,其主要目的,一為籌畫續修或重修宜蘭縣誌;二為針對噶瑪蘭三十六社進行調查工作;三為其他如開蘭 一九五週年紀念活動,以及宜蘭縣相關歷史文獻資料的蒐集工作等。而屬於非法定行政體系所屬單位的「文獻小組」,後來又轉化為「宜蘭縣史館籌備處」,再到正 式成立「宜蘭縣史館」。
在「文獻小組」工作十個月期間,初期正苦於二二八受難家屬難找時。有一天,手持公文到宜蘭縣立文化中心一樓秘書室時,看到坐在椅子上正在書寫回函的秘書桌 子上有一封署名李本璧,並附上電話、住址及身分證字號的陳情書。當時宜蘭市公所退休的李本璧先生建議宜蘭縣政府要為因二二八事件而受難於頭城媽祖廟前的宜 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先生等七人設立二二八紀念碑。無意中獲此消息,在經過秘書的同意下,影印一份陳情書,並立即和李本璧先生電話聯絡。
二二八口述歷史工作不包含「文獻小組」的工作範圍,這是下班後筆者想要做的一件事。記得有一天打電話給李本璧先生,想要和他約定時間、地點以進行口述和錄 音工作時,電話的另一端傳出李本璧先生和他兒子發生爭吵的聲音,因為基於保護其父親的立場,他兒子不希望也不贊成其父親談及令人心生恐懼的二二八事件。但 是,那一天,李本璧先生還是穿著西裝、皮鞋來到筆者租屋處接受訪談。
日治時期即在當時的宜蘭市役所工作的李本璧先生對當時的宜蘭二二八事件相當清楚,而且對受難於頭城媽祖廟的七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或了解其家庭狀況。後 來受難家屬一位一位地出現了,就是李本璧先生介紹筆者認識的。可以這麼說,《噶瑪蘭二二八》一書之所以能夠從無到有,李本璧先生是主要貢獻者。
有了李本璧先生的幫忙、帶路下,筆者以一個講著和宜蘭腔調完全不同的外地人,在當時雖然已經解嚴,但白色恐怖氣氛依然如烏雲般壟罩台灣社會的情形下,想要進行像二二八事件這種令人畏懼,又擔心情治單位是否會表達不同意見等顧慮下,才能把工作一步一步地往前推動。
宜蘭縣因蘭陽溪的關係,分為溪北和溪南,有了李本璧先生,溪北部份就容易解決了。溪南部份的突破點主要是當時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的楊基山先生,有一天在 《中國晚報》上報導張雲昌受難的故事,並附上張雲昌先生相片及其妻子楊純女士和兒子張憲明先生的照片。這個報導,對當時正找筆者討論成立二二八團體相關條 文和章程,本身也是受難家屬的葉朝清先生而言,可以說又找到一個同伴了。之後,筆者和沈秀華小姐便前去採訪、錄音。
同樣住在羅東的另一位受難者是陳成岳先生,當時其日籍妻子和兒子早已搬離令人傷心的羅東而住在台北,透過二二八發生當時為宜蘭高中學生的陳兆震先生,因為 來自中國且會講日語的趙桐老師,是陳兆震先生的宜蘭高中老師,二二八當中被槍殺於蘇澳鎮南方澳海邊,為此已接受過筆者的採訪,所以能夠和陳成岳先生的獨子 陳章弘先生認識,並在陳兆震先生家進行採訪、錄音的工作。
回想起來,當時進行二二八口述歷史工作,心裡著實有些擔心和畏懼情治單位是否會出手作梗或加害,後來家裡電話確實有些怪異聲音,筆者和葉朝清先生及張憲明 先生因二二八採訪工作而互相認識,並同時籌組並成立「宜蘭縣二二八關懷聯合會」,後來改為「宜蘭縣二二八受難家屬關懷協會」。在籌組或成立後的定時或不定 時的內部會議,均在不同地方,在當時情治單位確實有直接到受難家屬家裡或筆者的租屋處表達關切,以及蒐集相關資料。
《噶瑪蘭二二八》一書,受訪者總共二十六位,受難家屬有十三位,見證者有十三位。事實上,據目前所得到的訊息,當時宜蘭縣所有受難家屬約三十至四十位 之間,有些受難者或受難家屬無從查起,這些人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動而消逝在台灣歷史當中。至於十三位見證者當中,有三位接受採訪、錄音,針對受訪內容則同 意刊出,但只同意冠姓不署名字。在當時的台灣政治氣氛下,這是個人的選擇和意見,我們都應該尊重,當時確實也都徵詢過其立場。此外,有一位經張憲明先生介 紹,而進行採訪、錄音的一位受訪者,在受訪過後的隔天早上,打電話給筆者,並建議筆者當作其本人未曾接受訪問,不要發表其受訪內容。基於避免心生疑慮和不 必要的擔心與困擾,透過張憲明先生,筆者將錄音帶送給當事人。
另一方面,宜蘭的二二八歷史工作和其他縣市比較,則多了一件插曲。記得在「文獻小組」工作時,四個成員當中,當時只有筆者不是教師,其他三位都是國中小老 師,且深受宜蘭縣政府的重視。有一天,上班當中,聽到同事說出:「二二八事件宜蘭不是爆發點,死亡人數也不是很多」,並以此來質疑為什麼台灣各縣市都要興 建二二八紀念碑。當時全台灣各縣市二二八受難家屬正互相聯繫並積極要求政府做出合理公平正義的回應。有一天,來自其他縣市和宜蘭縣受難家屬一起前往宜蘭縣 政府拜訪當時縣長游錫堃先生,會談間游錫堃先生不知何故竟然也說出:「二二八事件宜蘭不是爆發點,死亡人數也不多」這句話,當時對縣長頗有期望的受難家屬 和筆者聽了這句話後,均相當不解與失望。為此宜蘭縣二二八紀念物或紀念碑便一直不見蹤影。為了表達興建紀念碑的意願,宜蘭縣受難家屬便在也是受難地點的蘭 陽大橋邊施放高空氣球,並在上面寫著「歷史可以原諒,不能忘記」十個大字,以此展現其立場和決心。
十九年前的《噶瑪蘭二二八》一書的「緒論」結尾處,筆者為何不寫出是誰在受難家屬面前說出「死亡人數不是很多」的原因,乃是基於保護游錫堃先生立場, 很多受難家屬也是隱忍下來,維持不給游錫堃先生難堪的立場和愛護之情,為了這件事,「宜蘭縣二二八難家屬關懷協會」和縣政府曾有一段緊張關係。
台灣社會從二二八苦難當中,一步一步地走出來,然而我們到底在當中學習到多少對人性和生命尊嚴與價值的提升和肯定。承擔歷史黑暗苦痛的受難家屬也一位一位 地衰老、凋零了。年輕一輩又從何得知要從歷史的苦耐當中學習建立民主、自由及建立能夠創造、維護人民幸福和利益的國家呢?這一切似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 走。
十九年前和十九年後,同樣面對二二八事件,筆者的心情似乎有所不同,回想起來,在當年的採訪過程當中,曾經和當時還是未婚妻的太太林秀蕙小姐一起到嘉 義採訪郭勝華小姐,並在郭小姐的帶領下,前往其父親郭章垣先生的墓前哀悼及拍照留念。以及之後的種種事情,筆者其實在人生的路上學習到很多一般人無法看 到、體會到的歷史經驗和故事,這是上天對筆者的一種眷顧和歷練,可以說點滴在心頭。
最後,感謝亦師亦友的張炎憲先生,以及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一片對台灣歷史工作的熱誠。當然陳朝海先生那一通電話真是打得太好了。
2011年1月16日